民国,可谓风起云涌的乱世,《民国那些事儿》以“史话”的形式,存逸闻之鲜活,取史书之大气,刻画出了一大批政客与文人的群体雕像。本文摘选民国几位著名教授的轶闻趣事,以飨读者。
胡适:“胡说”白话文
认识胡适,可以从“胡说”开始。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黑板上的几个字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黄侃:“三不来”教授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两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后来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对黄侃颇多嘉许,劝其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写。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无意中藏了“绝命书”3字。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他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辜鸿铭:北大讲台上的狂儒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一Whiskey(Dosto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
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来源:网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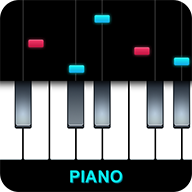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