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罗从他藏身其后的
皮埃罗从他藏身其后的巴士后探出脑袋看着街道,看到所有等在那里的汽车和人都走了,连拦住他们的警察也离开了,不由得长出一口气。好哇。或者,不如说现在还挺好,趁他还没有真正开始害怕……
他离开车站,朝让-卢的房子走去,背上扛着背包。他有点紧张,尽管他曾经搭让-卢那辆名叫梅赛德斯的车到过这里很多次,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对路。他几乎没有怎么注意他们走过的路,因为那会儿他尽忙着说笑,盯着朋友的脸看。他和让-卢在一起时总是笑个不停。嗯,当然,不是所有时候,因为有人说只有傻瓜才笑个不停,他可不希望被人当作傻瓜。
不过,反正他并不习惯自己出门,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会出事,或者别的孩子会捉弄他。就像那波纳夫人的女儿一样,她牙齿歪歪扭扭,脸上还有疙瘩,她管他叫“白痴脸”。他不知道白痴脸是什么意思,他问妈妈的时候,她转身背对着他,但是他还是来得及看到她眼里涌出眼泪。皮埃罗对此并不太在意。妈妈的眼睛经常湿淋淋的,她看到电视剧最后两个人接起吻,响起小提琴,举行婚礼时总是这个样子。他真正担心的只是他妈妈湿淋淋的眼睛意味着他迟早得娶那波纳夫人的女儿。
半路上,他觉得很渴,喝掉了从家里带来的整罐可乐。他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本来是打算和让-卢一起喝的,但是天这么热,他口干舌燥,他的朋友想必不会介意这么件小事吧。而且他还有一罐巧克力嘛。
到达让-卢家时,他有点淌汗,心想要是带件T恤衫来换就好了。不过那也没关系。他知道让-卢在洗衣房衣柜里有一抽屉衬衫,专门用来在房子里干活时换。要是他的衣服湿了,让-卢会借给他一件,他可以等妈妈把它洗好熨平了再还给他。以前他在游泳池边,衣服被水弄湿,让-卢就借给他一件蓝色的衣服,不过那次他以为让-卢是借给他的,其实他是送给了他。
现在,他首先要找到钥匙。他看到大门里的邮箱了,上面写着墨绿色的让-卢?维第埃的字样,这颜色和门栅栏的颜色一样。他把手伸进栅栏,摸到信箱底部。手指触到有点像一把钥匙粘在干掉的口香糖上的东西。
他刚要把钥匙抽出来,就听到一辆车停在离大门不远处的地方。幸运的是,皮埃罗被一丛灌木和柏树遮住了,汽车上的人看不到他。他躲了起来,看到经常和警察总监在一起的那个美国人坐在一辆蓝色车里。那个警察总监再也看不到了,有人说他死了。皮埃罗悄悄躲开,没让那人看到他。要是被看到,那人肯定要盘问他在这儿干什么,然后把他送回家。
他沿着柏油路走开,一直藏着身子。他爬过那段陡峭的地方,爬的时候得倒退着下去,一边转过脑袋看路。他翻过栏杆,从灌木丛中隐蔽地爬了下去。从他这里可以看到让-卢的院子,他好奇地看着一群人在那里东奔西跑,大多数都是穿蓝制服的人,还有些穿警察衣服的和一些穿便装的人。那个到电台来,和别人说话从来不笑,和芭芭拉说话却总是满脸堆笑的家伙也在。
他藏在那里好一会儿,一直等到所有人都离开,院子里没有人为止。最后一个走的是那个美国人,他没有关上车库门。皮埃罗幸好有自己在这里照料朋友的房子。他得赶快进去看看唱片是不是都还好,关好车库的门,然后才离开。否则,谁都可以溜进去偷东西了。
他慢慢站起来,四处打量。他蹲了这么长时间,膝盖一阵酸痛,脚麻得刺痛。他在地上跺脚,好让刺痛消失,他妈妈就是这样教他的。皮埃罗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想好了一套行动计划。他不能从他现在的地方走到院子里,因为他正站在通向大海的陡坡中间。所以他得先爬上铺沥青的路,从那里再爬过去,看看能否翻过大门。
他调整好肩膀上的背包,准备好攀爬。
他从眼角看到底下的灌木里有些动静。他想,可能他搞错了。那里不可能有人;不然他应该看到他们过来。不过为了搞清楚,他又蹲回灌木丛,用手扒开树枝,好看个清楚。有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觉得自己肯定看错了。然后,他看到的确有东西在灌木丛里移动,他把手搭在眼睛上,免得被太阳灼伤。
他惊愕地张大嘴巴。他的下方正是他的朋友让-卢,他穿着绿色和棕色交间的衣服,看起来好像是土地和灌木丛的一部分,肩膀上背了个帆布包。他正从一丛灌木中往外爬。皮埃罗屏住呼吸。要是按他的性子,肯定会跳出来,喊叫自己在这里。但是这样估计不是个好主意,因为要是警察还没走,有人会看到他们。他决定爬高一点,朝右边爬去,等到被堤坝遮住身子后再叫让-卢知道他在这里。
他无声无息地爬动,设法模仿下方的朋友的动作,后者正从灌木丛中灵巧地爬出,一根树叶也没碰动。最后,他爬到一个再也不可能看到更远处的地方,心想这里从房子那边可看不见了。他下方鼓出来一块石头,很小,但是正好可以让他站在上面和让-卢打招呼而不让警察看见。
他小心地朝下爬去,想接近那块石头。他曲起腿,抬起胳膊朝下跳去。他的脚一接触到地面,那块易碎的石头就被他的体重压断了,可怜的皮埃罗发出一声惨叫,朝深渊滚去。
弗兰克在漆黑的黑暗中慢慢前行。
他仔细检查隧道之后,发觉高度足够他爬过去,于是毅然钻了进去。这个姿势并不舒服,不过也是最安全的一种。他苦笑着想,要说“在黑暗中摸索”,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场合了。
他感觉自己像只受过训练的猎狗一样爬行,很快,身后传来的微弱光线消失了,他只能在彻底的黑暗中爬行。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但还是看不到任何东西。他右手举着枪,身体贴着左侧的墙,微微朝后让着身体,好让左手作为前进的向导,确保没有什么障碍或者更糟糕的陷阱。要是在这个不知名的洞里出什么事,他可能从此就从人间神秘失踪了。
他一点点地小心前进。他的腿开始感到酸痛,右膝盖尤其疼痛不已。大学时代打橄榄球时,他扭伤了右膝盖的韧带,从此不能再打球,而且也断了他成为职业球员的美梦。他过去总是让肌肉保持良好状态,以应不时之需,但是最近他锻炼得很少,况且现在这样的姿势连举重运动员也吃不消。
他微微颤抖了一下。洞里非常阴冷。不过,由于紧张,他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它从腋下冒出,浸湿薄薄的衬衫。隧道里充满潮湿的树叶和水气味以及湿水泥墙的味道。他时不时在管道接口处撞上一段扎进来的树根。他第一次碰上这种树根的时候,猛地把手一收,仿佛被烫到一般。隧道显然通往外部,很有可能有什么动物会一路钻进来,在这里搭起窝。弗兰克并不害怕,不过碰到一条草蛇或者一只耗子显然也不是他的最高理想。
他希望这场漫长的追
他希望这场漫长的追捕终于到了尽头,他的幻想能够变成现实。每次他提到非人,设想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一场慢慢的、偷偷摸摸的、小心谨慎的前进,周围到处都是潮湿和寒冷,耗子丛生。这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调查的象征:慢慢的、令人疲惫的慢速进展,完全在黑暗中进行,指望着有道微弱的光线能带领他们钻出黑夜。
让我们在阳光中毁灭……
在彻底的黑暗中,埃阿斯在《伊利亚特》中著名的祈祷突然涌上心头。他在高中学过它,那大概是一百万年前的事了。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在大船附近交战,朱庇特布下大雾,阻挡希腊人的视线,他们危在旦夕。就在那时,埃阿斯对众神之父发出祈祷,这个发自肺腑的祈祷并非为了活命,而是要求至少可以在阳光中被毁灭。
他感觉到隧道变陡,顿时又绷起神经。脚下铺好的路面变得倾斜。有可能是隧道已经被毁坏了,也有可能是事故造成的,也许他们在建筑过程中发现有石头阻挡,不得不向下挖了一点好绕过去。
他决定坐下,就这样滑下去。他更加小心翼翼。弗兰克担心的并不是坡道。非人想必已经在这里来回通过很多次,不过他必定娴熟得多,因为他熟悉这里的地形,而且可能还有手电用。
而他呢,他却陷于完全的黑暗中,对前方或者周围的东西都一无所知。他担心的是让-卢。他非常清楚这个人狡猾无比,诡计多端,他很有可能为潜在的进攻者准备了陷阱。
他又想到让-卢?维第埃的真实身份,最重要的是,是谁创造出他。现在已经澄清的是,他不是个出于软弱沮丧而任疯狂驱使,干下一系列罪行,吸引报纸和电视的注意的精神病人。这个仓促的结论在很多案件中都是合理的,但这远远不能解释非人的案件。别的罪犯都是些普通、焦躁的人,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比他们更强大的力量驱使下行动的。他们戴上手铐时,都会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
非人却不是。这个人与众不同。水晶棺材里的尸体证明了他的疯狂程度。他的思想毫无疑问装满让最冷静的心理学者也不寒而栗的想法。但是还不止如此。
让-卢强悍、聪明,准备有序,训练有素。他是天生的格斗家,带着不可思议的轻松杀死了约肯?威尔德和罗比?斯特里克,后两个人都经过良好的锻炼,有着运动家的体格。他在自己的房子里杀死另外三个警察的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点。他体内仿佛存在两个人、两种互相对立的性格。也许最好的描述是他用不自然的声调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人而非人……
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人,绝对不容小觑。弗兰克并不觉得这样加倍小心有什么不对。有时,谨慎与否决定人的生死……
他对此非常清楚,因为唯一一次他本能地、不假思索地冲进门去,结果导致他在一场爆炸和15天的昏迷后在医院里醒来。要是他忘记了这事,那么他身上遍布的伤疤也会随时提醒他。他不希望冒无谓的风险。不管今后是否还当警察,他认为自己都必须这样做。他为了一个女人必须这样做,这个女人正在尼斯候机厅等待着他。他为了哈瑞娅特也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
他继续往前爬着,尽可能不发出声响。谁知道让-卢这会儿在哪里,不过他并不排除他还在隧道那头的可能,也许他躲藏在那里,等他离开。毕竟,地下洞穴总不能一路通到蒙顿。它必定通到房子东面,山上的斜坡上的什么地方。
那里可能还是一片混乱。警察的路障,成排的汽车。人们钻出汽车,踮起脚尖想看个究竟,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互相打听。混迹于这样一个人群中不会太难,是啊,让-卢的照片出现在全欧洲所有报纸上,电视新闻里。但是弗兰克早就对这些措施失去信心。一般人可能只会随意看看别人的脸。让-卢只需要剪短头发,戴上副墨镜,就可以轻而易举挤进人群。
不过路上还满是警惕的警察,他们瞪大双眼检查着。警察不会这么大意。他们可能会对一个从下面10码远的灌木中出现,一路爬上路边的人感到怀疑。哪怕瞎子也会对这个感到疑惑,何况连日的事情已经让警察们绷紧神经,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敢放过一个。所以弗兰克不排除这人会找一个人少的机会再从藏身之处出来的可能。
他继续往前爬。裤子在隧道底部摩擦的声音听起来像尼亚加拉瀑布一般响亮。摩擦的地方开始发疼。他停了一下,换个舒服一点的姿势,决定开始爬行。他竖起身子,手机突然发出嘀嘀声,仿佛安静的乡村夜晚突然响起教堂钟声。这个信号有可能暴露他的行踪,不过也提醒他出口近了。
他在黑暗中转着眼睛,相信看到了一点光线,它就像黑板上的白粉笔道道。他设法加快速度,同时仍旧保持警惕。他的心脏跳得更加剧烈。他左手在水泥墙上蹭着,右手手指压在扳机上,膝盖痛得不行,但是面前已有一道隐隐的光线,以及一个绝对不应当低估的人存在。黑板上的白粉笔道道舞动着,在空中延伸,他越靠近,白粉笔道道就变得越宽。弗兰克意识到隧道在一丛灌木附近到了头。他能看到透过树枝传来的光线。可能有风吹动树叶,所以光点在他饱受黑暗之苦的眼里看起来好像萤火虫一般。
突然,他听到外面传来绝望的尖叫。弗兰克的谨慎像扑克牌搭起的城堡被扇子一扇就倒塌一样,顿时被抛到脑后。他以这个位置能允许的最快速度,冲到掩藏着隧道出口的灌木丛那里。他把树枝拨到一边,缓缓探出脑袋。出口正好在一丛相当大的灌木后面,水泥管道完全被掩盖在树枝中。
尖叫声还在继续。弗兰克慢慢站起来。他的膝盖诉说着一种他宁可不要听懂的语言。他环顾四周。灌木周围相当平整,可谓山坡上的一个天然平台,周围长着有细细树干的树。藤蔓缠绕着这些树,树根部分长满低矮的灌木,与棺材统治的那片地方相比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他背后是那两幢一样的房子和它们精心打造的花园矗立在上方。公路在他左面上方50码的地方。弗兰克看到上方边上一点,有什么东西在他和柏油路当中的斜坡上移动。一个穿了件绿色衬衫和卡其色裤子,背上扛了个深色帆布包的人影正小心地穿过灌木,朝上方的栏杆处爬去。
弗兰克哪怕过了一百万年,也能从一百万人中认出这个人。他举起枪,用两手握着瞄准。他把目标放在瞄准器正中央,终于喊出了他这么久一直渴望喊的话。
“站住,让-卢!我的枪已经对准你了。别逼我开枪!举起手,跪下,不要动!按我说的做!”
让-卢朝弗兰克方
让-卢朝弗兰克方向转过头来。他没有任何认出他或者明白他的意思的表示,而且似乎一点也不打算按他的话做。他想必看到弗兰克手里的枪,却继续朝左边爬去。弗兰克的手指紧紧扣着格洛克的扳机。
尖叫声在继续,又响又尖。
让-卢低下头回答,“皮埃罗,抓紧点,我来了。别怕,我马上来救你。”
弗兰克朝让-卢说话的方向看去,发现皮埃罗正紧紧抓着一棵长在路边的小树。男孩两脚扑腾着,想找到可以站住的地方,但每次一踩到岩石上,松脆的泥土就碎开了,男孩发觉脚下无处可踩。
他下方是一段非常陡峭的斜坡。虽说不是真正的悬崖,但是一旦皮埃罗松手,他就会像个玩具娃娃一样一路滚下山,摔进下方200米处的峡谷,肯定就没救了。
“快呀,让-卢。我坚持不了啦,我的手痛!”
弗兰克看出男孩已经没有力气,声音充满恐惧。这声音里还充满对让-卢、主持人、杀手、恶魔的声音、他最好的朋友的信任,仿佛相信他一定会来搭救自己。弗兰克明白让-卢在做什么之后,松开了扳机。
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去救皮埃罗。
逃跑可能是他原先的计划,本来一切可能进展顺利。他在隧道里等待,直到所有骚乱都平息后,他便溜出来,再一次逃脱警察的追捕。然后,他发现处于危险中的皮埃罗。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皮埃罗会在那里,吊在一根树枝上,用受惊孩子的声音呼救。也有可能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总之他立刻判断了形势,作出选择。现在他正在履行自己的决定。
弗兰克感到体内一阵郁闷的愤怒,这是他屡受挫败的后果。他为了这个时刻,等待了那么长时间,然而自己全力寻找的这个人正在射程之中时,他却无法开火。他把枪重新举起,瞄准镜中正是让-卢的身体,他正朝悬挂在树上的朋友方向赶去。
现在,让-卢已经赶到皮埃罗身边,趴在他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和男孩之间只隔着后者刚才摔下时撞出的小坑。他很难伸出手去拉住男孩。
“我来了,皮埃罗,”让-卢用他温和深沉的声音对男孩说,“我来了。别紧张,没事的。不过你得抓紧点,不要慌张,好吗?”
皮埃罗尽管身处危险中,还是用他的典型方式认真地点点头。他的眼睛因为恐惧瞪得大大的,但是他相信朋友一定会救出他。
弗兰克看着让-卢把扛着的包放在地上,开始抽出皮带。他一点也不明白他打算怎样救出皮埃罗。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站在原地看着,将让-卢始终保持在射程之内。
让-卢抽出了皮带,突然他们听到一声有点像吹箭筒发出的刺耳嘶嘶声,一股尘土在他身边激起。他本能地弯下腰,趁机逃过一劫,因为啸声和激起的尘土正好在刹那间和他擦肩而过。弗兰克猛地转过身朝上看去。在斜坡顶上,栏杆的这一面,站着瑞安?摩斯上校,他站在齐腰灌木中,手举一杆带消音器的自动枪。
这时,让-卢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跳到乳香灌木中消失了。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他仿佛突然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瑞安?摩斯想必也一样感到惊讶。他继续往让-卢藏身的灌木丛开了好几枪,直到把子弹射完。他取出空弹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满的塞了进去。一秒钟之后,他又可以继续开火了。他慢慢朝下爬去,仔细观察周围的灌木。弗兰克把格洛克朝他的方向移动过去。
“从这里滚开,摩斯。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丢下你的枪,滚蛋吧。不然就帮我抓住他。首先,我们得为吊在那里的男孩着想,先别管别的。”
上校继续举着枪往下爬。他一刻不停地检查周围的灌木,同时回答,“谁说这和我没有关系?我说有关系,奥塔伯先生。我是决定先干什么的人。首先,我要除掉这个疯子,然后我再帮你摆弄那个白痴,要是你需要的话……”
弗兰克用枪瞄准瑞安?摩斯粗壮的身体。他几乎按捺不住射死他的欲望,这和他想射死让-卢的欲望差不多一样强烈。
“我再说一遍,放下枪,瑞安。”
“要是我不干呢?”他干巴巴地冷笑一声回答。他的声音充满挖苦。“开枪?然后你打算和人家怎么说?射死一个你自己国家的战士来救一个杀手?还是给我放下你那苍蝇拍,学学怎样……”
弗兰克继续瞄准他,一边尽可能快地移向皮埃罗。他从未陷入这样一个需要做这么多选择的处境。
“救命,我再也没力气了!”
皮埃罗痛苦的声音从下面传来。弗兰克放下枪,尽可能赶到让-卢刚才在的位置。他感觉到灌木像恶魔的手一样从灌木中伸出来,试图抓住他。他时不时转头看看瑞安?摩斯的行动。士兵仍旧在小心翼翼地朝下方爬去,举着枪,狐疑的眼睛在灌木中搜索让-卢的踪影。
突然,摩斯身边的灌木活动了。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灌木中跳出来的绝对不是刚才埋下身子躲藏的那个人。他不是让-卢,而是一个从地狱中被放逐的恶魔,放逐的原因是他使别的恶魔害怕。他身体不自然地紧绷着,仿佛体内突然生出一只狂暴的野兽,把强健的肌肉和敏锐的感觉安放到他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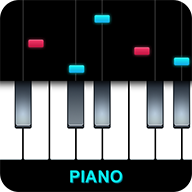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