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来讲,我不是一个嗜辣的人,却也算一个喜欢吃辣的人,究其原因,应该是现在的生活水平比从前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每天肉林酒海、肥甘厚味,消磨了味蕾的敏感,便也增加了对辣的渴望,心底以为这几年凡与辣有关的菜系比如川菜和湘菜等、与辣有关的食物比如重庆火锅和麻辣烫等能够大行其道的一个因由。
北方因气候干燥,且算是苦寒之地的穷山恶水,似乎没有什么吃辣的历史与文化,这样探究起来,我该算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吃辣的人,这就与家人很有些格格不入的意思。儿时在农村生活期间,看到左邻右舍的顽童拿着馒头,抹上厚厚的辣椒酱再加上葱或者蒜,我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后来成家,在家中掌勺之际,父母亲都对辣味的东西持观望态度,我料理出的象水煮鱼、辣子鸡之流的菜,他们是很少问津。妻是大快朵颐,时间长了就以为子女很是不该不顾及老人的口味,于是,家中的辣椒啊、豆瓣啊之类的东西便束之高阁,留与虫儿去消受去了。
外地的菜流入一个地方,必定要与当地的饮食习惯相互影响乃至于结合,我的说法就是那菜总归是不正宗的了。东北的川菜和湘菜与本地菜结合得略显紧密,或者干脆说改良太过了——我的感觉一是菜码加大,二是该辣不辣,吃这样的菜全然没有什么过瘾的感觉,若遇师傅手艺一般,便以为那菜也就是东北家常菜多放了些辣椒而已。菜码加大是我辈之幸,可以饕餮一番,可也局限了那多点几样小菜品尝的自由,终归是一个普通人,享受归享受,还是脱不了精打细算的窠臼。可那该辣不辣,却经常让一些老饕可恨。这个原因我也作了分析,北地人实不善食辣,这算是一个因由,其二,北方的辣椒固然是和湘蜀之地不同的,就如同橘生淮南则为橘而橘生淮北则为枳一样,倘若没有那样的环境土壤,断是长不出那样的味道的。比如我去年在北京工作的那三个月时间,一位处长是四川人,一位同事是湖南人,便大有食必选川湘的意思,就连偶尔选中的江西菜,也都是辣得到了位,让我着实地过了瘾,却又更痴迷于辣味。平白地让回到黑龙江的我多了对辣味的渴望。
自诩为对吃有别样感情的馋人的我来说,自然是不能放过任何的机会去寻觅街头巷尾的美食,我的心里顽固地认为真正的好东西是在江湖,江湖的边边角角才会有真正的好味道,草根不在江湖又能在哪里?那些看似狭小的店面一定是缺少富丽堂皇,但谁又知道一把破琵琶后面藏着如何哀婉动人的曲?循着这样的道理,大的馆子除却应酬之外,我便很少去,一个是银根问题,另一个,我真想满足的是自己的嘴却不是什么脸面。
吃说起来也是一门学问,我尚算是一个门外汉。三五好友,袒胸裸背,赤膊相向,酒碗见底,桌盘狼藉,自然有一种野性的豪气;一二知己,丝竹声声,浅吟低唱,诗酒相和,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情;孤身一人,对月邀影,三杯两盏,醉睨世间,更是一种豁达的境界。于是,与各种环境相匹配的食物便很有一些说法了。吃字拆开了,一个口,一个乞,无外乎求得满足口腹之欲尔。再往深里面想一层,怕是还有一种心情在里面,不然,回忆起往事来,为什么偏偏会想起和某人在哪里吃却忘记了满桌的珍馐美味呢?
却有一样东西让我每每想起,念念不忘,虽尚未成瘾,却也每一念及、垂涎欲滴。有的菜是天生的贵族,有的菜是天生的草根,而有的菜,却是阳春白雪可登大雅之殿、下里巴人可入草民之堂,就象豆腐一样,如得王侯将相的口,也进得平民百姓的腹。窃以为我喜欢的这样东西就是,高朋满座可充珍馐之数,就算是一人独酌,亦算是难得之美味。
世间有一个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就是凡事要讲究个平衡,从我的寻觅和对美食的理解上看,也算是有了些须的印证。随着南菜北渐,那些南方的食品也都涌了过来,也渗入到了平民的生活当中。比如北人喜食鸡,讲究个炖法,却重在吃肉而轻了食汤,南人煲鸡却是要个火候十足,将那鸡骨及肉弃置一旁,单单去喝那汤。仅从这点上看,北人的粗砺和南人的细腻便可见端倪。再比如,南人讲究食鸭,甚于食鸡,究其因,盖中医认为鸭肉性微寒、味甘咸,具有滋阴养胃、清肺补血、利水消肿的功效,说到底,吃是为了养生服务的,而北人则不然,自小我听到大都是鸭子全是骨头没有肉之类的说法,落了个鸭子无甚吃头的印象。即便是弄来吃的,无外乎一个炖,或干炖鸭子,或炖酸菜,或炖土豆之流,似乎无煲汤一说,也更加没有将鸭子拆散了专门吃某一部位的说法。北京的烤鸭算是一个特例,虽然可以将一鸭烤了片了卷饼蘸甜面酱而剩余的骨肉拿来做汤,但更细一些的似乎便少见了,而且烤鸭的肥腻实在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一道厚重大门。
我所念念不忘的,便是鸭的某一部位——脖子,并进而爱屋及乌地喜欢了鸭头、鸭舌之类。若要真的较起真儿来,我最初接触的该算鸭头,不是有一个对联么,“丫头啃鸭头,丫头嫌,鸭头咸”。慨叹古人的奇思妙想之际,便添了对鸭头的渴望。而后数次在饭店吃了一些熏酱的鸭头,渐觉这类物什似无专门去饭店开荤的必要,便开始将视线瞄向了街头的小铺。北地的哈尔滨街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冠有外地名头的招牌,比如北京水爆肚,比如上海本邦菜,比如陕西羊肉泡等等,这些自然都是一些需留置店内吃的正餐,我所寻找的是另外的那种随时可以拿得出来的吃食,加上对鸭的渴望,便有了还算明确的目标,什么武汉精武鸭颈王、久久鸭颈王、川府鸭颈王之类。试想着左手持杯痛饮,右手拿鸭猛啖,真个是把酒临风、痛快淋漓,满足了刁钻的舌头,也打理了倦怠的心情。
对于一个吃客而言,舌头无疑是最公平的。我自然是不能在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之后再亏待了自己的舌头。别小看这七零八碎的鸭子零件,既然吃到了嘴里,自然不能什么都当菜。人的习惯养成之后就成了惯性,在不知道多少次的挑剔和比较之后,我的舌头认准了川府的那一系列,按照我的排序,最辣的是鸭肠,而后是鸭头、鸭舌、鸭颈。每次享受之后反思,盖是那独特的辣和特别的香征服了我。若是按照阴阳调和的理论,鸭消却了椒的燥热,椒消却了鸭的寒凉,使二者短处尽消,长处益彰,不温不火,可享美味又不伤身,岂不是一桩美事?曾经在翻看网页的时候看到一则消息,说是食辣能够让人快乐,从这一层面上说,食辣不仅仅是满足口腹的欲望,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和依赖,想到这里便开始觉得自己高尚起来,把凡俗的东西上升了层次。
我还是要强调我不是一个嗜辣的人,可那辣味却深深地入驻到了心里,时不时地蹦跳出来,挑逗着我的味蕾,让那样酥酥麻麻的渴望充斥在唇齿之间,于是充满了挑战那样的辣的期待。前一段出去吃烤翅,特意选了一个BT辣,结果证明,我依然不算一个能吃辣的人,那样的辣直入身体,回转过来灼热了气息,炙烤得鼻腔都火辣辣地疼,头上大汗淋漓,口内剧烈地刺痛,火烧火燎,凉凉的啤酒便成了救命的稻草,忽然发现,原来那辣只是在翅上面的厚厚一层辣椒,我所挑战的不是吃辣的烤翅,而是看嘴和胃能承担多少辣椒。
川府鸭颈却全然不是如此。
那辣是入眼,热烈的颜色,似火在烧,一下子映入了眼帘,撩拨着心绪,撩拨着身体里最本能的那根神经,直接就把眼神给拽过去,红红的,源自火红的辣椒的火红的颜色,却又把那鲜红凝练提纯,加上时间的沧桑,暗红不张扬,却又尽显厚重,彻底地预热着大脑,留给人的,就是剩下猛烈地燃烧;那辣是入鼻,扑鼻而来的是别样的香气,热烈却并不浓密,清冽却并不清淡,洒脱不缠绵,缠绵不旖旎,从鼻入肺,充分地调动着一切感知器官,沿途所经过的细胞早已沉沉醉去;那辣是入口,那样的辣味是单纯的辣椒所不能比拟的,在浓稠的汤汁之中经过了火的熬炼,把产自南国的辣椒的辣味和香气全部浸润到肉里,到骨里,丝丝缕缕的肉丝之间,满溢着渴望的味道;那辣是入心,经过了眼,经过了鼻,经过了口,那味道就由鼻到口,由肺到胃,轻轻地拍打着渴望的心脏的律动,一忽轻轻挠拨,一忽重重揉搓,闭上眼睛,不再呼吸,停止咀嚼,忽然发现,原来辣味竟然如此地神奇,庆幸着,把本能的吃变成一种吃的享受的感觉真好……
看武侠小说看得多了,很喜欢里面那句无招胜有招的话来,简单的一句话有着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或者真的是万物一理,往往是最简单而不繁复的东西隐藏着深奥的道理来,当我在吃川府鸭颈说出一句无椒胜有椒的时候,朋友哈哈大笑,可不是么,那么一半一半的鸭头、一段一段的鸭颈,轻轻巧巧地汲了辣椒和那么多中药料的滋味,进而变成了自己的内容,就象那煲鸡的汤,吸尽了鸡的精华,不也算是无鸡胜有鸡么?
漫漫的冬日,温一壶酒,切上几只鸭头、鸭颈,看着窗外大雪飘飞,让那样的香辣沁入心脾,暖一暖漂泊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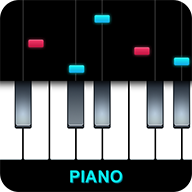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