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好了:地球上人口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而是“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一个隐藏在美国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电脑中的虚拟世界!创建不过4年,“第二人生”的“人口”已接近1000万,“国内生产总值”约6.7亿美元,足足相当于一个世界排名第200位的经济体。其财富主要源于最初由林登实验室提供的虚拟土地的买卖,或是游戏玩家提供的虚拟物品及服务的交易。交易通过“林登币”实现,这种虚拟货币可以兑换成真正的美元(目前的行情是266林登元兑1美元),因而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居民”在其中发了真正的大财。
这类新型创业者的发迹之地是一片大小不一的岛屿,岛上有森林、群山、冰川、沙漠和城市,有豪华别墅、俱乐部、商店和古迹名胜……现实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就环境而言。至于这里的“居民”,你只需下载一个免费软件,就能联入这个新世界,一睹他们的真颜。那是一些三维动画人物,是真实玩家的虚拟化身,玩家可以通过电脑键盘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在显示屏上的活动,例如去理发、到新潮时装店添置行头、到美容院做护理,还可以去电影院、交友会——说不定虚拟朋友还能发展成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总之,让虚拟化身如同真人一般生活,把自己投身到一个由二进制编码构成的第二生命之中。这很容易办到,因为在“第二人生”中,我们能找到现实社会的大部分构成元素:剧院、媒体、知名商业品牌、政党……随便举几个例子吧。著名的路透新闻社就在“第二人生”里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同样知名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即将在其中安家落户;巴黎的老佛爷百货中心在“第二人生”为其一所美容院揭幕;而最近,法国海军甚至在“第二人生”通过虚拟化身之间的接触来招募真人军官。更甚者,连科学也抵挡不住“第二人生”的诱惑。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普渡大学,甚至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都在“第二人生”设立了校园。欧洲的大学,如英国的莱斯特大学、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法国的土伦大学也纷纷效仿……更不用说美国的两个著名研究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它们在“第二人生”里各拥有一个岛屿。
研究者摇身变成造物者
问题是,研究现实事物的科学跑到这个虚拟空间来干什么?烘托真实气氛?不仅仅如此。事实上,对于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生物学或遗传学等学科来说,“第二人生”是研究人员用来交流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的一个新途径。但要在其中进行科研,那就不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及其与自然规律大相径庭的荒诞特质对于上述学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它却适于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这些学科也将“第二人生”视为一个强大的交流工具,专门传播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的虚拟学院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可以通过虚拟化身在那里阅读他的着作或聆听讲座。不过对于这类学科来说,这种世界首先并尤其是一个可以进行各种大规模仿真研究的绝好实验室。以至于在今天,没有一个虚拟世界或电子游戏能逃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种志、人类学、流行病学,甚至精神病学的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
要知道,第二人生、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哈宝旅馆(Habbo Hotel)、安特罗皮亚世界(Entropia Universe)、模拟人生(Sims Online)、太空战士(Final Fantasy)、天堂(Lineage)、There.com等虚拟世界在全球拥有数不尽的玩家。一个新兴的大众文化娱乐行为,其本身就会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兴趣,以了解有什么样的人参与、如何参与和为什么参与。不过,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虚拟世界也许能够作为研究现实世界的参考模型。他们认为,要揭开我们社会运行机制的奥秘,要研究他人的存在如何决定或改变个体的行为,只要在某个合成世界中做几个实验,然后就可以把结果推广到现实社会中了。
这想法很荒唐?倒也未必。在这些虚拟世界里,我们游戏,我们协作,我们创业——有时还能发财致富,我们交友,我们恋爱,我们结婚,我们分手……一句话,我们“生活”着。因此,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虚拟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教授吉姆·布拉斯考维奇(Jim Blascovich)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将“第二人生”之类的虚拟世界视如“研究人类行为的完美工具”。正如印第安纳大学博士生马修·法尔克(Matthew Falk)所说的,它们前所未有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整个社会放入试管,在完全受控的情况下进行实验”的机会。的确,借助虚拟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实现所有实验者的夙愿,即对研究对象的完美控制。如同造物者般,研究人员将能随意更变虚拟化身的体貌特征,如“皮肤”的颜色、身高、性别、发型、衣着……他们还可以改变实验的环境参数,让实验在海边、在山上,或是在城市里进行,颠倒日夜,变换天气……总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世界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观察。
现实与虚拟的相似之处
更何况在这些虚拟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各个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数据库里。没错,这里是“老大哥”(Big Brother)的天下:你所做的事情、常去的地方、碰到的朋友、所说的话……这样说吧,在这里你没有任何隐私。从而研究人员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掌握和重复各项实验条件。理论上,体貌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社团如何形成,或环境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但问题是,游戏开发商们很少愿意向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他们对我们的研究不感兴趣。”马修·法尔克认为。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奇。游戏开发商有责任确保游戏不受任何的干扰,以保证虚拟替身们的清静。不过,以“第二人生”为代表的人生模拟游戏并没有将研究者拒之门外,这是因为“第二人生”不只是游戏。林登实验室甚至表示“欢迎所有的科学家”,而且“对研究者使用‘第二人生’进行科学研究感到非常之荣幸”。就连向研究机构提供有关虚拟替身的所有数据的问题,林登实验室也作出了肯定的表示,并称自己在这方面是极度透明的:“我们已经公布了许多关于玩家性别、所在地,以及联网时间的统计资料。”
那么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是否找到了他们的乐土呢?某些研究者对此坚信不移,并确信能够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的观察结果用于现实社会。第一批研究结果也有力支持了这一观点。美国斯坦福大学传媒学院心理学家尼克·叶(Nick Yee)在2007年2月所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第二人生”里,两个男性虚拟替身在交谈时,两人之间的距离比两个女性虚拟替身在同等条件下交谈时要远,而且他们相互对视的频率也比女性虚拟替身之间的要低。这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情况完全一致。
另一个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相似之处:拥挤在“第二人生”里带来的不适丝毫不逊于它在巴黎地铁里制造的效果。当两个虚拟替身相距很近时,他们会避免对视。这太让人吃惊了!同样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杰瑞米·白朗松(Jeremy Bailenson)认为,“很大一部分行为方式被我们带到了虚拟世界。”哪怕以一个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虚拟替身为掩护,其行为似乎最终还是会暴露我们的真实面目。巴黎第十三大学教育科学博士生、虚拟世界人文科学观察所成员文森·柏利(Vincent Berry)便指出:“在虚拟世界中不存在匿名。对虚拟替身的选择,其姿态,其游戏、交谈的方式,其幽默感,所有这些形成了一套修辞模式。有意无意地,我们会去解读这些修辞模式,最终达到人以群分的结果。很多因素会决定群体的形成,年龄、社会阶层……”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
流行病学家的理想模型?
那么,虚拟世界是否真的可以用来作为现实世界的可靠样本呢?对于文森·柏利来说,这一天还很遥远:“那些认为能够用来自‘第二人生’的研究成果定义现实世界的研究者忘记了一点,虚拟世界的环境背景与现实生活相差太远,无法推此及彼。在某个环境中获得的能力与该环境紧密相连,不能生搬硬套到另一个环境中。”说白了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个腼腆的人,迷上“魔兽世界”后,可能在游戏中变得热情奔放,但不等于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改变其腼腆的本性。话就这样说死了吗?不一定。因为尼克·叶和杰瑞米·白朗松即将发表的最新研究恰恰表明,在虚拟环境中获得的能力完全可以转移到现实世界中。两位研究者借鉴了认知心理学上的一个经典实验,该实验曾证明人类行为的一个特性:对损失的厌恶。在这个实验中,每个参与者都要与面对的实验人员分享一笔钱财。参与者提出分享的方式,对方接受或拒绝。如果建议被接受,钱财就会按照建议的方式分配。如果建议被拒绝,那么双方都将分毫无取。实验进行两次。首先由虚拟替身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一些参与者选择了比对手个头大的虚拟替身,而另一些选择了个头较小的虚拟替身。实验结果表明个头的大小对谈判的方式起到了直接的影响。那些选择了个头较大的虚拟替身的参与者相比于选择了个头较小的虚拟替身的参与者,更不愿意妥协。尤其是随后,当实验在现实生活中重复时,每个人,至少在谈判的最初,都保留了在虚拟世界中所持的态度。这就证明,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能力向现实生活的转移是存在的!
看来,研究结果向现实社会的推广并不像文森·柏利所认为的那样全无可能。这也促使众多的研究者,如吉姆·布拉斯考维奇,持“即使不是很确定,也还是要尝试一下”的态度。这也是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朗·巴里瑟(Ran Balicer)的态度,他所从事的流行病学正好是一门人类行为学和微生物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实验既可以是虚拟的——比如虚拟替身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是现实的——比如通过显微镜观察病毒。对于这位流行病学家来说,“任何一个虚拟世界都是我们能够期望得到更好的人类互动模拟的地方。”他认为,对研究病毒的传播和蔓延而言,这些虚拟环境比目前流行病学所运用的模型要好得多。因为普通模型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人类行为进行极为简化的再现,而在虚拟世界中,每个虚拟替身的背后都是一个血肉之躯。
阿尔顿,为实验而设……
“我认为,” 朗·巴里瑟说道,“虚拟世界是流行病模型的下一个发展步骤,而且这一步应该尽早实现。”所以在2007年3月,他就发出了“科学工作者与游戏研发者迅速联手开始共同合作”的号召。但到今天为止,这一合作还没有实现。在“欢迎所有的科学家”的林登实验室,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号召……虚拟世界的大门并不像研究人员所期待的那样敞开。因此,爱德华·卡斯特罗诺瓦(Edward Castronova)的团队在去年决定,创建自己的以研究为目的的虚拟世界,他们为之取名为“阿尔顿,莎士比亚世界”(Arden)。一方面,“阿尔顿”是一个以15世纪英国为背景的角色扮演游戏,可以与“魔兽世界”竞争。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供社会科学进行实验的工具。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作为这一团队的成员,马修·法尔克承认困难重重。首先是经费问题。“‘魔兽世界’或‘第二人生’都是高薪雇佣一大批计算机高手,持续工作好几年才开发出的像样的产品。这是一个实验室、甚至一所大学所做不到的。”更何况拨给“阿尔顿”项目的大学经费在最近又被砍掉了,自那以后“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成了义工”。然而,经费还只是第一个障碍。即使成功开发出“阿尔顿”,还必须吸引足够的玩家,把它营造成一个值得开展研究的虚拟世界。因为虚拟世界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它们的数目已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某些专家断言其中的一些将难以为继。
时间,经费,意愿,还有方法……科学研究在把虚拟世界转变成试管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这些缺憾可全都实实在在。因此眼下,这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还远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成果。而社会科学研究者目前对“第二人生”或“魔兽世界”的迷恋能否持久呢?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万一不能持久的话,那么或许还有一个可供他们消遣的课题,那就是了解为什么虚拟世界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甚至在他们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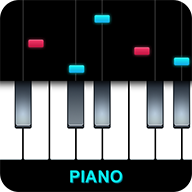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