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页
王巍(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
在各种传媒和各位专家的解剖下,国美之争的来龙去脉和戏剧变化,早已是路人皆知,关于国美的讨论已经演化成一个商界立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但很多围观的人往往在不了解国美之争的技术常识便摇旗呐喊般的进场助威,很多参与讨论的人也无视辩论对方的观点,只是自说自话的立场表态。更多的评论家在捕捉一点表面现象后便武断地对其中一方兴师问罪,以观念对抗观念形成意识形态的辩论。我认为,大家讨论的不只是国美之争,而是中国企业转型到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要素,更是中国工商企业文明的进化过程的阵痛。
有五种力量制约着国美之争的观察框架:大股东、管理层、基金股东、市场规则、传媒与公众,这也是现代公众公司的运行结构框架。黄陈之争不仅是老板与经理人之争,也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争。同样,贝恩资本与黄之争是也股东之争。这是基本的事实,也有现成的解决争端的法律和财务平台,特别是香港的市场规则久经考验,并不需要我们为之大动干戈。
问题在于,传媒和公众这个维度是最难协调把握的,立场不一致,当然观点不同,争论自然要提升到道德层面,这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里也是同理。这次国美之争之所以如此被关注,恰恰是在中国的价值信仰体系早已坍塌的格局下,我们无所适从,无所顾忌,因此也无所寄托,只能各自建立自己的道德制高点,而道德的混战在市场上却是无解的。因而,我们要有所提升视野,才能更好梳理我们的思路。
其一, 是非判断与利害分析。 合理合情合法是所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希望同时实现的结局,因此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幻境,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任何商业行为多是机锋百变,虚无缥缈。
在国美之争中,我们看到的多是逻辑论证和心理分析,动辄涉及到人物臧否和品德定性。分析家多是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心理脆弱,对方稍有不敬词语,立马上纲上线的反驳。传媒界更是自恃话语威权,随便抛出一个低级的论点,便不容分说地演绎到裁判者的地步。企业家在言语暴力下被迫,或被诱不得不匆忙选择立场,保黄或保陈,这又无意中陷入自己前后矛盾的困境:大多数企业家同时是股东,也是管理者。
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思维习惯是泾渭分明,步调一致,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与所谓敌我友的选择,始终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下,真正的问题是商业利害的比较和选择,是非判断并不重要,妥协才是发展的动力。只有将是非判断调整为利害分析,现代公司的生存价值体系才能形成。
试想一下,商业历史上政治历史上哪有什么大是大非的事情呢,后人否认前人的事情还不是层出不穷么?我想,这也是当局号召我们要与时俱进的真正涵义。所以,情理分析暂时还是放在一边,让我们既存的法规优先吧。如果法规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情理原则,也要按照程序来修正法规。
其二,公司治理的理解。公司治理包括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些词汇进入中国已经有些日子了,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共同的语境平台,新瓶里都是装的各家的陈酒。
我在国企和民企的上市公司中都参与过公司治理委员会,也有机会参加国际机构和政府监管的讨论,看惯了大戏和小戏,这其实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工具而已。冲突的多了,各方的磨合成本太高,约定俗成就形成了一个彼此遵守的框架,美其名曰公司治理规则。一旦市场变化,各方博弈力量有大的增减,公司治理就要被重新洗牌,大可不必对各方唱高调特别较真的。
股东无论大小,经理人无论强弱,都倾向于以自己的利益单元来约束公司的运行。东家们千方百计地防范他人将“我的公司”偷走,掌柜们则小心翼翼(弱时)或明目张胆(强时)地建立特殊规则控制“我的公司”,而大多数小股东或员工则无意也无力参与实践自己的应有的权利,只好坐山观虎斗,不时地表演自己的受害者地位。
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以自己的裁判地位常常进场改变规则,以公司治理名义操控公司按符合当政者利益的方向发展,据说是维稳。在最少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派些独立董事们进场监督办事。
这次国美之争中,陈晓给管理层分股权,办了黄光裕该办的事情,黄光裕否决基金董事,董事会再否定股东会决议,这个连环交易都是以公司治理的名义大张挞伐,同时也的确限定了对方的动作范围,客观上提升了公司治理的地位,给所有围观者上了惊心动魄的公司治理实战课。还是别拿公司治理说事儿,关注环境变化中,各方博弈的真正动作吧。
其三,创业者与管理者的双重心态。中国这一代企业家都是同时具有两种心态。作为创业者,他们需要不断地打破规则网罗,顶着进监狱和法院风险前行。这个变革的社会没有提供一个安全制度,这导致他们的多疑和善变,也造成了无数的阴谋和韬略。同时,作为管理者,他们又要不断在自己把控的空间内建立各种纪律和规则,甚至要借来杰克韦尔奇和德鲁克等大师来装神弄鬼讲管理的故事。
这就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情,不断地破坏规则,还要不断地建立壁垒。在这样的环境下,空泛地对企业家们进行诛心之论,道德抨击就太过迂腐了。轻易援引国际惯例,居高临下地评点本土企业家的得失,也是不够中肯。政府未能给自己的公民和企业家创业家提供基本安全感,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职。
与其妖魔化企业家们,动辄谴责创业者的阴谋和管理者的背叛,还更要关注如何建立一个商业秩序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就是安全性。
第二页
维稳不应当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可以是很多具体的指标。例如,这个社会能否真正惩处欺骗股东和公众的造假者和背叛者,例如唐骏博士和李一道长?进一步,如果姑息那些明目张胆地窃取中小股东利益,背叛公众信托责任,巧取豪夺公众资产的行为,那么,所有的创业者和管理者都是不安全的,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对法制社会的侮辱。
其四,市场制度的考验。市场的制度是在参与各方利益的不断冲突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在精英官员的设计里实现,更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知道分子)的道德说教中实现。市场的成长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成功和失败的过程,监管当局和社会公众都应该给市场博弈者必要的空间自我调整,允许当事人的各种作为,即便是失败之举。
这次国美之争的大批围观者都通过评论表达自己的立场,给我的感觉是,大抵在海外留学背景和在国际经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多是支持陈晓和管理层的。而在国内江湖闯荡经年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多是支持黄光裕的。双方对贝恩资本的介入方式和动机上均有强烈批评的共识,只是角度不一样。
这种两军壁垒的阵势的确激励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进一步自我认知定位,反过来又将原本模糊的阵线截然划出来了。这样是非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就再次弥漫着讨论,一个很脆弱的市场制度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我们能不能不必如此理性和聪明,给市场制度一个基本空间?这次政府没有干预是非常大的进步,也许是因为国美是香港上市公司的缘故吧。
市场制度不是一个空洞的方向和观念,而是技术细节和动作。我们要关注黄光裕在狱之身,能否得到作为企业家的基本待遇,要关注贝恩资本是否公正履行对基金股东的承诺和对国美公司股东的承诺,要关注陈晓团队作为受托人是否公正地给自己一份市场报酬和股东回报,要关注中小股东如何在香港市场规则下表达自己的取舍,要关注冲突双方对国美公司在目前竞争格局下如何建立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
不应用道德谴责和伦理批评来干扰市场制度的自组织运作,动辄鼓励行政的干预,或者煽动商业环境中的民粹主义情绪。
其五, 契约精神的考验。这次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就是“背叛”,这是指违约,而且是不道德的违约。
在整个事件发展的链条上,不同人在不同时段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切片来分析。是陈晓背叛黄光裕,是黄光裕部将背叛黄光裕,是黄光裕背叛贝恩资本,还是黄光裕或陈晓或贝恩资本背叛了全体中小股东?这样纠结着一系列不同的契约,包括商业契约,也包括道德契约(受托人的承诺等)。一旦将道德牵进来,所有契约都是一堆烂账,剪不断理还乱。
好在这个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香港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国美之争在这个市场上的前例数不胜数,我们的证监会还无意公开干预这个市场。违反商业契约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即便是巨额赔款,即便是入狱服刑,即便是资产缩水。以管理团队出走,或者放弃注入经营资产等理由来实施并购交易中的焦土战略,在资本市场上司空见惯,无碍制度稳定,也无碍契约精神的维护。
以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契约维系的商业社会便是一个稳定的商业社会,只要这个契约不是在暴力和特权下制造出来的。遗憾的是,我们有太多的契约不是平等商业谈判和市场博弈构成的,而是人为勾兑,特权压迫,资源控制等复杂因素下形成的,甚至国际资本也会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获得更有利自己的契约。但是,这是商业进步的代价,不能以暴易暴,还是要坚守契约,即便在一定时段内是不平等不公正的。
在国美之争上,契约是解决问题的底线,也是唯一的标准。当然,如果双方达成契约之外的妥协,也是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不应当是简单的撕毁契约。我们必须了解上市公司的公众兴致,国美不是黄光裕的、不是陈晓团队的,不是大股东的,不是“我”的,而是全体股东的,是“我们”的,这是一系列商业契约所约定的。
最后,传媒和公众的关注。 相对于当年的德隆集团、格林柯尔集团、华源集团乃至南德集团等这些曾高调出没于资本市场,最后突然销声匿迹的公司,国美集团应当是非常幸运的。
即便黄光裕身在囹圄中,黄光裕作为股东和创业者的基本职能仍然能够得到正常发挥。政府也没有下钳口令,或者超越权限的乱作为。这就成就了国美之争的公演,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围观并讨论,受教育,也去展现自己教育别人的才华。
只有在传媒和公众的关注监督下,争论双方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寻找自己利益的依托,寻求法律的支持。也正是在传媒和公众的持续关注下,市场制度和商业规则得以成为比政府介入更为公正有效的平台。
因此,我们应当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评论家分析家媒体和公众,他们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市场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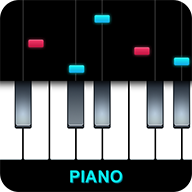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