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自横的心猛地抽紧了
周自横的心猛地抽紧了,尖锐地疼痛起来。他几乎已经可以透过时光的玻璃墙,清楚地看到童年的洛红尘:结着一对细黄的小辫,挥舞着两只细黄的胳膊,黑,瘦,小小脸孔上唯有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大得惊人。抿着嘴,可以整天整天地不说话,但是给自己发明了许多一个人的游戏,会坐在阳光下自说自话地讲故事,会将柳枝和荆棘草编成各种形状,下雨的时候,会叠纸船顺着水漂走,船里盛着落花和鸟的羽毛、以及童年的梦……
此刻的周自横,不再是公司里那个铁面无私的周董,而在不知不觉中转换角色变成了敏感多情的少年阿横,他一直幻想会有那样的一个妹妹,柔弱的,聪颖的,等着他来怜爱和保护的小妹妹。
然而,他在她的生命中出现得太晚了,竟然让她孤独地度过了那么长久的二十三年,是他的错,他错了,他该补偿她的。生平第一次,周自横的心里充满了温柔的护惜,全心全意地,急切地,想要对一个人好,不问代价没有理由地,对一个人好。
也许每个人都有付出和给予的欲望,只是有些人找不到付出的对象。自横认定了,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全心给予,那就是洛红尘。没有原因,不求回报,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感情,是前生注定的,是债。
神瑛侍者给绛珠仙草灌溉雨露,是心甘情愿;林黛玉将一世的眼泪还给贾宝玉,也是心甘情愿。
所有的感情都是恩,也是债。
梅绮仍在极尽刻薄之能事地损着洛红尘,把她的身世形容得污秽而罪恶:“……关于她妈妈的死,说法很多。她自己姥爷最常说的一种,就是她爸爸杀死了她妈,她爸是疯子嘛,也不知道究竟做了些什么,真可怕,总之洛红尘一出世她妈就死了,她爸也疯了,邻居都说她克,命硬,又说她八成是断掌,倒不知是不是真的。听她卖弄红楼梦那点故事,说林黛玉出身多么高贵,品格多么高贵,性情多么高贵,就好像她自己有多高贵似的。原来,她自己的出身这么卑微,和‘高贵’这个词儿,差了十万八千里……”
每一句话,都似一把刀从周自横的心上划过,使他一下一下地疼着——不是痛苦,是疼爱。梅绮对洛红尘的诋辱,只有使他对红尘更加充满同情和怜爱,更有保护她照顾她的冲动。他完全可以想象从小到大,她经历了怎么样艰难羞辱的成长过程;他更加理解了,她的态度为什么会那般独立、坚强、不卑不亢。
他恨不得立时三刻赶回公司去,把红尘紧紧地抱在怀里,告诉她:她所有的苦难都自今日结束,以后,他会好好地对待她,让她远离孤独与风雨,得到幸福!
然而洛红尘根本不领情。
总经理室里,洛红尘小脸绷得铁紧,一双眼睛晶亮得让人不敢逼视,戒备地质问周自横:“为什么要打听我家里的事?这与工作能力有关系吗?”
“我也是道听途说。”周自横有些惶愧,这对他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用了心,就会变得这样被动卑微,“偶然听说的,我只想告诉你,希望能够帮助你。”
“不需要。”红尘硬梆梆地顶回去,“如果总经理觉得聘用一个家族里有精神病史的人不方便的话,明说好了。否则,我不希望在工作时间谈论我的家庭。”
自横的心又一次抽痛。红尘的话让他同时接收到两个信息:一,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女儿,她自小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羞辱,以至于自我保护已经成了本能;二,她真是一个原则性强的女子,她和他,是不折不扣的同类人。
他只得道歉。从认识洛红尘起,他好像就在不断地道歉:“对不起,我并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如果你介意,就当我没说过……”
“我很介意。”洛红尘明明白白地打断,“好,我可以当你没说过,这次谈话不存在。周董,没别的事,我回办公室了。”
周自横被晾在了当地。前所未有的尴尬。前所未有地失落。前所未有的经验。
如果一个人没有原因地拼命想对另一个人好是前生的债,那么另一个人没有余地拼命拒绝这个人的好,是否就是前世的仇呢?
下了班,自横来到老友阿青的“火车头酒吧”消夜。
酒吧很小,是由两节废旧车皮拼接成的,桌椅都是从旧火车上搬下来废物利用的,连照明都是用的铁路上的提灯,四壁摆满了手摇电话,老式留声机,煤油灯等物事,一种粗犷的怀旧,野性的风情。
周自横是由欣赏阿青的品味进而欣赏这间“火车头酒吧”直到欣赏阿青这个人的,他们是纯粹的酒友,除了酒吧,从不曾在第二个场所聚会,也从不曾在阳光下碰面。
他们在一起,谈酒,谈色,也谈钱,但是从来不谈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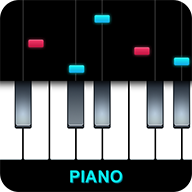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