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导演里,我一直很喜欢贾樟柯,这个小个子男人总是在 自己 影象世界里将各种的无奈和痛楚一起打包抛向你,纠结的情绪中给你展示生活的本质,和那些颇有些宿命色彩的隐喻。
第六代导演里,我一直很喜欢贾樟柯,这个小个子男人总是在 自己 影象世界里将各种的无奈和痛楚一起打包抛向你,纠结的情绪中给你展示生活的本质,和那些颇有些宿命色彩的隐喻。
三峡好人的故事很简单,在奉节的三峡工地上,一个男人,一个 女人 , 都在苦苦地寻找另一半,结局却完全相反,民工韩三明终于在16年后和自己的女人开始了新的人生,而女护士(对不起,我忘记了这个由赵涛扮演的角色在片中叫 什么名字,还是就叫她女护士吧)虽然也找到了消失了两年的丈夫,却最终决定离开。虽然一直是在讲述两个找寻爱的个体的故事,但导演显然也将自己的关照范围 扩展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地三峡,在整个观影的过程,除了感喟主人公的命运外,我更是对影片中那支离破碎的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影片中很多带有导演臆想色 彩的神秘主义情绪,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那些现实的和超现实的情景中。
影片一开始,韩三明被拉到奉节县某街某号他 前妻 家 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搞得手足无措,难道眼前的大土堆就是前妻的家?而之后他从旅馆老板的新家出来时我们再一次吃惊地发现,那仅仅是个桥墩改造的临时居 所,除此之外,就连很多空镜头里也充满了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废墟场景。这里已经成为了废墟上的城市,废墟就是这个城市主题的诠释。无论主人公走到哪里,故事 的行进中总是伴随着背景里楼房的倒塌和耳边传来的轰隆的巨响声,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奇迹总是在每分每秒钟赶着上演,而贾樟柯也借助片中拆迁办公室工作 人员的口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这是个两千年的城市,要在两年内就完全拆掉,这里边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片中两个极具象征意义甚至有些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头,更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回味空间。一个 是片中好几次出现的那个后现代雕塑般的“半边楼”,那残缺得颇具想象力的造型,好几次让我误以为那真的是一座雕塑,而导演刻意让它出现在几个场景中,我也 以为他是想表达和我一样的惊叹,然而之后发生的一切显然证明是我错了,这其实是导演一个精心的铺垫,终于在那场女护士靠着窗口失声痛哭的戏中,所有人都难 掩惊讶地发现那个楼飞了起来,和火箭一样。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地看到了位于镜头前的女护士的脸开始模糊,而镜头的焦点转向了那个像火箭一样点火起飞的“半 边楼”。
这样一部现实主义影片中,导演这样的处理显然有些冒险,它有可能让影片的客观和冷静毁于一 旦,但我却十分理解他这样的安排,这完全是影片前半部积蓄了很久的情绪总爆发,在这样大拆迁、大移民的城市中,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人们对一切 都充满着不安全感,你深爱的丈夫也许会在下一刻离你而去,你的好兄弟也可能在一场斗殴中就再也回不来,而你住的房子也许在下一分钟就成为拆迁的废墟,一切 的变化都是在顷刻间发生的,2000年的城市都可以在转瞬就从地球消失,这一切都如同坐着火箭一样刺激和加速度。
而对于人们的不安全感,贾樟柯还在影片结尾安排了一段高空钢丝的表演,再一次刺痛了每一个观众的心,当韩三明决定带着 妻子 离 开,最后一次审视这个身边的世界时,他惊奇地发现在两栋拆迁的高楼中间,一个工人正如高空钢丝表演一样,小心奕奕地挪移着步子,这个是拆迁工人的现实,也 是这个城市所有人的境遇,每个人都在走着钢丝,一不小心,生活就会将他们抛弃。于是有些人选择了艰难维持,而有些人则选择了自我放逐,就如那个“小马哥” 说的“现在的江湖已经不在是原来的江湖”。
与第五代导演的习惯于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哲学命题不同,第六代导演似乎更乐于去关注个体命 运的沉浮,而贾樟柯更是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影象诉求,就也许这是我喜欢他的根本原因。就像他自己在回答复旦学生的问题时提到的,80年代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 人的个体意识的复苏,在他眼里一切的戏剧性都不如人的生命力来得更有力量,更加真实和有质感。而《三峡好人》除了让我看到了他一直的坚持外,也发现了相比 以前电影,他开始更多地开始思考个人命运与现实更加深刻的联系,就像他告戒现代人的“我们不应该懦弱到连现实带给我们的刺痛感都不敢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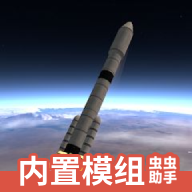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