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拉尔 在呼伦贝尔旅行的主要中转站
满洲里 草原上“升起”的彩色城市
根河湿地 盛产美景与美食
室韦 童话般的俄罗斯风情小镇
临江屯 充满蓝眼睛女人的热情
新敖乡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的简称
甘珠尔庙 呼伦贝尔一带最大的藏传佛寺
金帐汗 被莫尔格勒河养肥的草场
呼和诺尔 草原、马群、水泡子
莫尔道嘎 摄影师眼中的“秋美人”
白鹿岛 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养眼地”
小河口 吃鱼宴的好地方
金海岸 看呼伦湖的另一处地方
让心灵宿醉的大草原
飞机降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的海拉尔,迎接我们的除了碧波万顷的天然牧场,还有好朋友昆特勒,他的接风酒彻底击中了我困乏已久的内心和麻木不仁的内脏。杯盏之间,我就像一个流浪已久的孩子,竟生出一种找到回家之路的委屈和兴奋。
我们的目的地是陈巴尔虎旗的草原。出发前,我们在海拉尔市准备好了整箱的啤酒、白酒、一大堆火腿之类的熟食和充足的热情。在内蒙古,任意一片草原都可以充分容纳你的热情和梦想,而我们更像是一群坏蛋,一群心灵饥饿的狼,“心怀叵测”地奔向那诱人的草原。
当我们挤在租来的“微面”里抵达陈巴尔虎时,夜色已经降临,巨大的黑幕正在苍茫的草原上拉开。草原的夜晚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黑,浓得像墨,沉得似铁。卸下一路的疲惫和风尘,我们在预订好的蒙古包里痛饮了60多度的“草原白”,饱餐了正宗的牧区手把肉和羊血肠。酒酣耳热之际,眼神迷离的朋友们开始盘坐在温暖的火炕上,引吭高歌。
长歌当醉,长夜当醒。当朋友们抵足而眠的时候,我却鬼使神差地披上一床雪白的棉被走出帐篷,期待着与草原做一次神秘的对话。黑暗中冰冷的空气乘着不知来由的大风扑面而来,令我在瞬间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草原上的温差极大,昼夜之间就像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
时间似乎也被冻结,变得缓慢,直至静止,使我能够听到自己血流的声音。大地沉寂,如一只哑钟。天穹之下,星辰不再以群体的方式出现,而是一颗颗地垂下来,如同挂在睫毛上的泪珠。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令披着棉被的我慌忙举步,加快步伐,继而又仓皇地奔跑起来,仿佛一个失落的白色鬼魅,奔向我在白天见过的一座敖包。
敖包是草原上的路标,也是蒙古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地方。如果你曾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游荡过,就会很自然地理解一座敖包能够带给心灵的兴奋与慰藉,就像远航的水手终于见到灯塔一般。可那晚,我却像在另一种海上漂荡,感觉中并不遥远的距离却越走越远,或许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方向?然而敖包是不会拒绝一个世俗之人扑向神明的怀抱的,就像一个母亲不会拒绝孩子扑向她的怀抱。跌跌撞撞的奔跑之后,我终于看见了那堆比黑夜更凝重的石头。失明般的黑夜和失忆般的醉酒之中,我竟奇迹般地没有偏离方向!饱经风雨的苏勒德傲然挺立,无法分辨颜色的经幡和哈达在狂风和黑暗中乱舞。
那一刻,只一瞬间,我的酒醒了,心静了。
2
陈巴尔虎草原的蒙古包
在草原的深处是不会迷路的,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路,环顾四野,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如果不是有当地朋友带领,如果不是有敖包指向,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陈巴尔虎草原深处的土基和他的蒙古包。据朋友讲,这个土基本是大学里的高才生,却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要不今天也会是个白领什么的。
千百年来,草原都是寂寞而单调的,牧民为能够迎来远方的朋友而备感高兴。虽然现在的牧民几乎都有了摩托车或汽车,但是热情好客的传统却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的汽车刚刚停稳,那个叫土基的男主人便迎了出来,看年纪不过40岁。
土基的家在草原上算是相当典型的那种:白色的蒙古包用红、蓝色的木头架子支起,黑色的烟囱从蒙古包顶部探出;包的旁边是木栏围成的羊圈,看着不大却足能装下上千只羊;包的后面停着几辆首尾相连的搬家迁场用的“勒勒车”,和传统的那种不同,现在的“勒勒车”上都安装了铁皮箱柜;再有就是竖立在包后的发电风车,在大风中疯狂地旋转着。
蒙古包里的陈设很简单,也很整齐,迎面并没有看到牧民家常见的成吉思汗画像,也许是主人比较年轻的缘故吧。土基拿出银碗为我们倒上奶茶,这在草原上是最高的礼遇了。牧民平日自己使用的都是城里买来的木碗,但家家都备有这种被称为“孟根阿雅嘎”的银碗,在婚丧嫁娶、迎宾送客,或是家庭聚会时拿出使用。而那银碗中的奶茶,则是草原牧人每时都离不开的饮品,用砖茶、鲜牛奶、盐和水熬成。一碗奶茶,一把炒米,几块奶豆腐或几块手把肉,构成了牧人最经典的一份食谱。茶罢搁盏,土基带着我们去看他的羊群,那些白色的生灵在不远的草坡上游荡,仿佛在绿色天空中缓缓飘过的白云。这里水草丰美,当地的牧人也比较富有。不过一旦遇到天灾或疾病,牧民的损失也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发生。草坡的另一边,一群马在牧马人的驱赶下走了过来。土基笑问我们想不想骑马,大家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这些仅有骑马留念经历的城里人,哪里来的驾驭这些彪悍的蒙古马的能力,只能在脑海中幻想着成为一个牧马人,手执套马杆在草原上驰骋。
回到蒙古包,女主人已煮上了一锅手把肉,还笑言道:“半小时前,这锅里的羊还在草地上撒欢呢。”蒙古牧民做手把肉是百分之百地清炖,别说花椒等香料,就连盐巴都放得很少,吃的就是“新鲜”二字。土基按照最隆重的礼节,用蒙古语说了一串欢迎词,而女主人和孩子则手捧哈达和美酒,为我们一一斟酒、献歌。酒很容易就喝高了,土基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还不停地强调说自己也曾经是个大学生。离开的时候我们送给土基一块包头用的方巾,他很喜欢,说男人用手帕围着头的感觉很摇滚。
3
甘珠尔庙旁的那达慕
新巴尔虎左旗的草原因那达慕大会而提前沸腾起来。平日深居草原深处的牧民,现在都穿上节日的盛装,或驾车或骑马,纷纷向甘珠尔庙云集。这里是那达慕的传统举办地,庙旁的千百顶蒙古包炊烟袅袅,女人们忙着切炸面果、做马奶酒,男人们忙着练摔跤和射箭,十几岁的孩子们则匍匐在马背上,为赛马比赛做最后的准备。当晚还放起了烟火,所有人都跑了出来,年轻而强壮的牧民们随着花炮的爆响而放情高歌,狂欢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幸亏当地的朋友对一切了如指掌,第二天早早地就把我从帐篷里叫醒,赶赴那达慕的主会场。后来看着各个入口拥堵的人群,心想:要想进来真比登天还难。雄壮的军乐声标志着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古装的骑士快马加鞭地疾驰而过,然后出现了拉着“勒勒车”的庞大牛队,车上载着装饰精美的蒙古包,观众开始狂热地叫喊。朋友说:那帐篷象征着当年成吉思汗远征的大帐。接下来是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面具舞,有些年迈的牧民还自发地祭祀起敖包来。这是很古老的习俗,据说如果人们高兴,山水神灵也会随着兴奋起来,给牧区带来好年景。
搏克手们穿着镶有银钉的坎肩、紧身的短裤和做工上乘的皮靴上场了,健硕的身体一展无遗。搏克的比赛规则其实非常严酷,几十对选手同时对搏,不分年龄,不分体重,一跤定胜负,容不得半点含糊。几个回合下来,搏克手的身上已经满是搏斗时留下的红色印痕,我不禁咋舌:“为什么不穿厚一些?”身旁的牧民解释说:因为曾有一名高手所向无敌,但最后却被认出是个女人,于是从此以后,所有的搏克手都成了短装。
后来发现有的搏克手的脖子上戴着五彩的项圈,朋友说:“那叫章嘎,摔跤赢了就能得到一个,草原上的男人谁不想戴上章嘎?”据说在过去,一个搏克手想要戴上“章嘎”,就必须在有512位选手参赛的大型那达慕中获得冠军。现在虽然没那么严格了,但它依然是草原英雄的象征,这一点,从牧区姑娘们紧盯不放的眼神中就能了解到。一个英武的搏克手,在草原上也会被无数“粉丝”追捧。
赛马同样赏心悦目。参加赛马的都是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体重轻,马也可以跑得更快。参赛的马匹都是一副很可爱的打扮,马鬃被梳成了小辫,马尾巴也被精心捆束起来,据说这样方便奔跑。赛马场大概有三四十公里长,在古代这正好是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一声令下,骏马像箭射出,小骑士们竟是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之上!蒙人说:这样才能考验驭马的真本事。
比赛结束后,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去摸冠军的赛马,我也好奇地跑了过去。马背上的“小冠军”颇有绅士风度地向我伸出手,可面对着高大的马身和光光的马背,我根本没有办法爬上去。于是他的家人又从后面托起我,最终把我“安放”在了马背上。从“小冠军”的肩膀上望出去,草原上一片沸腾,就像刚烧开的一锅奶茶。
4
额尔古纳的农庄生活
草原上流淌着的哪里是河水,那分明就是奶水,即使在吃不上饭的艰苦时期,草原人民也有奶喝。“挤奶的时候,牧民就会舀上一勺子喝”,我的向导——“额裕俱乐部”的司机白师傅说,“不过你们肯定受不了,那就多尝尝奶茶,还有草原大雪糕。”他所说的最后一种奶制品无疑是这夏日草原上最有吸引力的食品,尤其是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头的“私家雪糕”。
摆在街头的冰淇淋机显得很简陋,机器旁放着一只破旧的铁皮牛奶桶,看上去似乎和美味没有任何关系。做冰淇淋的大妈将一只现做的蛋筒雪糕递给我,又乐呵呵地看着我把雪糕送到嘴里——毫无疑问,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奶味最浓郁的雪糕,绝非城市超市里的那些品牌雪糕所能比。看着我逐渐绽开的笑容,大妈不无得意地说:“这雪糕的原料全是我自家产的,没有人不说好。那些在黑山头办夏令营的美国人,一吧嗒嘴都是这雪糕的香味,两三天就开车过来吃一次,临走还装上满满一保温瓶……”
吃完雪糕的我也吧嗒了几下嘴,果然是满嘴的奶香。一直觉得草原上的饮食非常单调,额尔古纳市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印象——这“私家雪糕”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味觉快感还在市郊根河湿地旁的农庄里等着我呢。
前往农庄的道路很简陋,也很美丽。8月的草原上暖风习习,从路旁连绵不断的丘陵上吹过,金黄的油菜花田和墨绿的草场分割着这些山坡。道路的另一侧是蜿蜒流淌的根河,碧蓝的河水与低矮的柳蒿丛做着捉迷藏的游戏。通往农庄的道路也像是在和我们捉着迷藏,走错了两条岔道之后,我们才终于见到了隐蔽得很好的农庄入口,和有着俄罗斯血统的“农庄主“——王淳。
农庄不大,和它的主人一样,也是一副混血的模样:蓝墙红顶的两层尖顶小木楼,绿色窗台上的鲜花开得正艳,黄色的长椅旁一只白色的小猎狗懒洋洋地看着我们。坐进阳光充沛的小餐厅,王淳先为我们端来了一壶姜黄色的植物茶,味道清爽略带苦涩。“这茶是用黄芪和玫瑰泡的,全是在咱们河套里采的,败火利尿。”他所说的河套就是紧邻农庄的根河湿地,每年6月中旬野玫瑰花盛开。
当草茶的清香刚刚沁入心脾,满桌的农家菜肴便摆了上来。首先是“小笨鸡炖蘑菇”,小鸡就放养在后院,蘑菇随吃随到林子里采,几乎没有添加任何香料,味道却胜过最好的鸡精。接着是“干炸小鱼”,细长的叫“柳子鱼”,矮胖的叫“老头鱼”,全是刚从根河里打上来的冷水鱼,外焦里嫩,鲜美异常。还有“煎蛋”,乳黄色的蛋饼里夹杂着一种绿色的植物,那是遍布根河两岸的柳蒿的嫩芽,味道略苦十分爽口。再有就是“蘸酱菜”,除了黄瓜、大葱,还有一种叫“婆婆丁”的菜叶,其实就是蒲公英的叶子,蘸酱生吃特别清火。
“这河套就是一个大菜坛子,什么黄花菜、野韭菜、柳蒿芽、稠李子??都不带断茬的。”放着舒适的公差不干,躲在这个偏僻的农庄里颐养天年的王淳,在无意间道破了根河农庄生活的真谛,那就是靠天养人,靠河吃饭。
“住在这样的地方,人根本就不想走了。”王淳那一脸的满足表情,成为他这句话最好的注释。
5
临江屯的俄式狂欢
乘坐“额裕俱乐部”的大切诺基,我们驱车前往室韦附近的临江屯。美丽的乡间公路依着额尔古纳河一路蜿蜒,仿佛飘荡在绿色丘陵间的两条彩带,一蓝一黄。河道很窄,对岸的哨兵了望塔和俄罗斯村镇都在一望之内。
还没来得及“消化”这满目的风光,临江屯就已经到了。如果没人提醒我,我一定会以为自己正身处某个俄罗斯的小镇:满眼全是原木搭建的木刻楞房,木栅栏里“列巴花”开得正好,在房檐下乘凉的“俄罗斯大婶”向我这个异乡客投来好奇的目光??砖泥搭建的“列巴炉”则是整个村子的标志,每家的院里都必定会有一个,直到今天,起早做列巴面包还是村中妇女最基本的日常劳作之一。
听说有“远方的客人到来”,73岁的老人姚殿华赶来和我们聊天,他更愿意我们称呼他的俄文名——米葛莱,无疑这个名字也更符合他的长相。和村里的大部分老人一样,他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的爸爸从山东到这里淘金,认识了我的妈妈。俄罗斯女人喜欢中国男人,能干,喝了酒还不打老婆。”
米葛莱是这样解说他的身世的。现在,老人的儿子在莫斯科做鞋生意,他说:“歌里唱的那个莫斯科郊外,我玩过好几次……走,饭桌上说去。”
我们投宿的那家主人早已用丰盛的俄罗斯菜肴将饭桌“装点”停当。米葛莱像来到自己家一样,招呼我们就坐。桌上的酒杯已经斟满“莫茅酒”,老人二话不说就仰脖痛饮了一口,“古斯曼!”老人由衷地赞叹道,意思就是“香”,又转头对我们说:“你们不是要体验俄罗斯风情吗?这白酒就是俄罗斯风情。”听到这话,在座的人都乐了起来。陪同我们的朋友说,村里的人都非常朴实,如果客人没有喝醉,那他们就会认为是没有喝好,是他们没有尽到主人的责任。
“喝好了吗?喝好就玩一会儿吧!”听到这话一桌人都欢呼起来,一起动手把餐桌抬到客厅的角落,手风琴的音乐声也及时地响了起来——那是狂欢的信号,根本不用招呼,所有人都在客厅中间手舞足蹈起来。米葛莱也丝毫不为年龄所困,举着酒杯踩着曲点,大声地用俄语唱起前苏联的老歌儿。乐曲稍停,大家就回到餐桌痛饮;乐曲又起,大家就又舞蹈开来。随着身体中酒精度的增加,屋子里的气氛也愈加热烈,到最后已经分不清是跳舞转晕了,还是白酒喝晕了。
妮娜是狂欢人群中舞跳得最好的一个,经常会半蹲下来跳那种哥萨克式的踢腿舞,要么就是拉着一个醉酒的男人疯狂地转圈,直到他晕头转向地败下阵来。曾在北京燕郊打工的她笑呵呵地对我说:“那会儿差点被北京的警察遣送回国,以为我是黑户,是没有护照的俄国人。”不过没过多久,她却自己把自己“遣送”回了老家,“在北京每天起床就在想今天要做什么,太累心适应不了,还是回来好,看看这气氛,多快乐……”
话音未落,手风琴的音乐声再次响起,妮娜也像条件反射一般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不由分说地拉上我冲向屋子中间。我说:“喝多了,跳不动了。”她说:“跳多了,就不觉得喝多了。”手风琴一响,脚就痒痒——这就是生活在临江屯的俄罗斯族。在如此气氛的感染下,再拘谨的客人也免不了要痛饮一番,“放肆”一下。
6
大兴安岭的使鹿部落
在将近一整天的颠簸之后,我们终于在凌晨第一次走进了那片神秘的白桦林,走进了鄂温克人的故乡。长途的奔波并没让我们觉得辛苦,或说并不值得叫苦,比起鄂温克人曾经走过的迁徙之路,我们的跋涉实在算不了什么。
静静的森林,潺潺的溪水,在林间穿梭的晨光??这纯净的风光让我们兴奋不已,却让同行的坤特勒变得格外安静。她就是由这片白桦林养育长大的鄂温克人,工作以后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不过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仍是那么熟悉和了解,敏捷的步伐就像一只驯鹿。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她的舅舅家。
她的舅舅达瓦不在家,这个季节大部分的鄂温克男人都在猎民点上。猎民点是鄂温克人在山里牧放驯鹿的地方,也是他们在大山里的家。驯鹿是鄂温克人的生命,与这个狩猎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鄂温克人爱驯鹿就像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为每只鹿都起了名字。达瓦舅舅的两只驯鹿因为参加过那达慕,所以一只叫“那达慕”,另一只叫“大会”。每当搬迁,清脆的鹿铃就会响彻整个大兴安岭,上百只驯鹿浩浩荡荡地驮着鄂温克人的希望,从一个猎民点迁往另一个。
森林狩猎和饲养驯鹿锻炼出鄂温克人强壮的体魄,男女老少都能在山林里健步如飞,而且走到哪里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熟悉兴安岭的一草一木,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在达瓦舅舅居住的猎民点,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斜仁柱”。这是一种圆锥形的临时住屋,高约5米,由二三十根碗口粗的松木搭建而成,外面覆盖桦树皮和帆布,看上去很像印第安人的“提皮”,也常被称为“撮罗子”。达瓦热情地拥抱了他的侄女,又将我们让进了“斜仁柱”里。里面空间很小,光线也很暗。达瓦舅舅说,晚上他要组织整个家族为我们举行篝火晚会。
在“斜仁柱”里喝过奶茶,坤特勒领着我们去看额尔古纳河。她在林子中间健步如飞,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我们甩在身后。好在额尔古纳河离“猎民点”并不远,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浪花,没有起伏,仿佛是静止的一般。这条穿行于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呼伦贝尔境内的河流是鄂温克民族的母亲河,以前山林里的猎民驾着桦皮船在河上捕鱼,据说这样的船行驶时没有一点动静,不过随着鄂温克人陆续迁出大山,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会做这种树皮船了。
夜晚降临,达瓦舅舅组织的家庭篝火晚会在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小溪边举行。火苗将幽静的溪水映红,一名叫玛利亚·索的老妇唱起了古老的祈愿歌和祝福歌,而年轻人的歌声就要欢快许多,有鄂温克民歌、俄罗斯歌曲,也有蒙古民歌和流行歌曲。
在《敖鲁古雅小夜曲》的歌声中,我认识了放暑假回来的妞日卡,她是目前这个部落中学历最高的一个女孩,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她说:“我原来的名字叫妞拉,我们部落有个萨满也叫妞拉——你知道萨满吧?有些像巫师——她非常有名,是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个萨满,大概100岁时去世的。后来玛利亚·索姥姥就说你不要叫‘妞拉’了,叫‘妞日卡’吧。对于新名字我也十分喜欢,我想自己是不配叫妞拉的,妞拉萨满我见过,很慈祥,很智慧……”
我曾经见过萨满使用过的神鼓、神槌,据说萨满的神是乘着神鼓飞翔在天空的。但我没有见过妞日卡所说的妞拉萨满,也没有见过萨满跳神,以后再见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了。山林中的渔猎生活或许将永远变成博物馆中的陈列,变成故事中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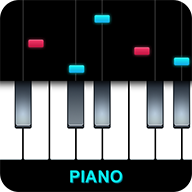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