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与艺术相距究竟有多远?带着这个疑问,南京当代艺术家郭海平住进了市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探索。他带来了画板、蜡笔、油彩、橡皮,还有茶和香烟,他让长期与世隔绝的精神病人们在放松的环境中,拿起笔,任意涂抹他们心中所想的任何画面。他说这是一场试
癫狂与艺术
癫狂与艺术相距究竟有多远?带着这个疑问,南京当代艺术家郭海平住进了市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探索。他带来了画板、蜡笔、油彩、橡皮,还有茶和香烟,他让长期与世隔绝的精神病人们在放松的环境中,拿起笔,任意涂抹他们心中所想的任何画面。他说这是一场试验,他要看看精神病人们究竟有着一个怎样的艺术世界。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
北京798“零工场”展览时,门口竖着巨大的海报
11月24日,北京798“零工场”,一批由精神病患者创作的绘画和陶器作品正在展出。展厅里捧场的人并不多。倒是有不少在798闲逛的老外被门口的海报吸引进来,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场“癫狂的艺术——精神病患者作品展”。
在中国,普通民众一向对精神病人有着极大的恐慌,而当代艺术更是被视为癫狂怪诞的近义词,然而,此次展览却试图将精神病人推上艺术创作者的席位。南京艺术家郭海平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出联系。
张宝玉作品《分裂》
张宝玉作品《怒吼》
张玉宝简介 张玉宝,男,32岁。从2005年春节出现无明显诱因的紧张害怕,说别人要杀他,拿着刀到处跑。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他参加绘画艺术后,对未来有了打算,想做个艺术家。开始和病友交谈,有了笑容。
点评:他的绘画流露出较多无意识显现,有一个主要特征:只要涉及人的形象,都是畸形的、残缺和痛苦的。相比之下,那些动物、蔬菜和蜻蜓却显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
长期以来,郭海平一直在关注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艺术的认知和常人有何不同。为此,他专门到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体验生活了三个月,希望通过对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的观察获得前人未曾有过的体验。结果大出其所料:“他妈的这些人太牛逼了!我以前认为艺术家和精神病人只有一纸之隔,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些艺术家跟精神病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跟他们比不得!”
《在天上看到的火车》、《曲线系列》作者 陈小军简介 陈小军,男,33岁。2003年因“凭空闻语,疑人害己,行为紊乱4年”入祖堂山精神病院至今。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
点评:看似简单,却变幻无穷的线条帮助他排解内心的郁闷和紧张。
站在王军的画前,很多人因为看不懂是什么而在画的角落里寻找标题。似乎是五朵绽放的花儿其实是王军画的水缸,因为他采用的视角是奇特的高空俯视。在王军的另一幅画里,同心圆以等高线的形式代表了医院门前的三座山,用小圆点画出树木,也是从天上看的。
几乎每个病人都有这样从高空俯视的画作,有的病人画汽车,呈现出来的是汽车的车顶,画房子能同时看到屋顶和四面墙。
郭海平说他在观看了病人们作画之后,切实感受到:精神病人都在天上。
郭海平这么解释,他们在现实当中太沉重了,必须脱离这个世界,因此就魂不附体,灵魂出窍。这也正是他十分羡慕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神病人跟艺术家相比,牛逼在率真,第二是精神的自由,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创作,释放出生命中的欲望和激情。”在精神病院里指导精神病人作画时,郭海平反反复复说这两句话。他甚至跟医生提出:能不能给病人们减药,使他们自然狂野的状态展现得更充分。
在郭海平的“弟子”当中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李丽。她因“智力低下、行为紊乱”在2006年被送入精神病院。这个一字不识的小姑娘最喜欢的事就是盯着一本书仔仔细细从头到尾地看,然后画出一连串奇奇怪怪的符号。这些画太过古怪,护士们看了都觉得好笑,认为和儿童涂鸦并无二致,郭海平却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
在他看来,李丽阅读的不是书籍,而是文字笔画间架结构中所传递的信息,平常人正因为纠缠于含义反而丢弃了文字本身。分析、盘算、领悟,这些在李丽的世界里都是没有的,摆脱了经验和知识之累,这是李丽给自以为正常的普通人上的一课。
与李丽这样“天书”般令人费解的作品类似,很多精神病人的作品非常酷,非常“后现代”,798的一位艺术家在看完展览之后感到惊奇的是:几乎每个病人的作品都可以对应现代艺术的某个流派。
在展会上被更多普通观众认可的,是张玉宝的画。一幅色彩明艳到几乎晃眼的油画《挣扎》,正中间是敦厚饱满的脸,没有鼻子和耳朵,表情沉静,而四周是一片橘红,布满了黑色的点。强烈的颜色对比让不少人联想起凡·高的作品。另一幅作品《怒吼》,是张宝玉自己命名的,一位参观展览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说,这幅画让她想起蒙克的《呐喊》,紧张、压抑、抽象,充满了对生命自由生长的强烈渴望。
在精神病院里,有一次旁人向张玉宝询问起所画内容的含义,张玉宝低声介绍:这个是关在铁笼里面的怪兽,这是没有香烟抽的感觉,这是一个人手牵着一只怪兽,他的头上有一个放大镜……这些图像都是从张玉宝脑子里冒出来的。这些话都被摄像机记录下来,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播放。
“他们的世界对于常人来说可望不可即,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要被我们的文明戒律所惩罚”,郭海平对精神病人艺术作品用“激赏”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他认为正常人不敢想不敢做不敢直接不敢自由发挥,被知识和经验所拘绊,和精神病人比实在差得很远。
祖堂山精神病院
祖堂山精神病院
为了进入精神病院,郭海平和医院沟通了十个月。他找了一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请了十几位行业知名专家轮番到医院游说,最终勉强说服医院同意进行一个月的尝试。
2006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郭海平正式进入祖堂山开始“癫狂艺术”的尝试。
祖堂山精神病院建于1952年,距城市中心1个多小时车程。在南京南郊风景区内,它与知名的弘觉寺仅一墙之隔。深秋,阳光普照,仍有寒意。从喧嚣的城市来到的人们,看到满目青山萧然,看着山上正大修的弘觉寺,看到隐藏在静寂中的祖堂山精神病院,会产生恍然的感觉。
这里每个病区都是独立的,男女分开管理。病人多在室内活动,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出来做操、运动。王玉,该院四病区的主任,在2006年偶然认识郭海平,因为常受到艺术界的朋友的熏陶,使她极为欣赏郭海平这一举动,同意与他合作。
“很多人对精神病人有认识的误区,害怕他们会伤害人,其实他们大多都不会。”在这所精神病院已有20年医龄的王玉,在病区穿梭着。这些病人都通过药物控制,处于病情的稳定期。看到王玉,会热情地打招呼;看到陌生人,会伸过头来看。但也有人一直在室内打转,走来走去,似乎什么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还有特别“热情”的,一见人就问东问西。有的甚至“噌”一下站到你面前,吓你一跳,“给我两块钱好吗?”还没等你回过神来,又转身走开。这种种反应,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是“异常的”。而当面对他们的绘画作品,你很难想象,那艺术源泉究竟来自哪里?毕竟“他们中很多是农民,从未受过任何教育,不曾拿过画笔”。
开始作画
画室设在6病区顶楼活动室。每天早上9点,医生把想画画的病人带来。郭海平开始收获了,收获惊喜、失望、辛苦,甚至恐惧。
一开始,病人们并不指望获得什么“艺术体验”。护士当场对病人说:你会不会画,不会画就不要画了!病人和病人也互相聊起来:就等于是来玩了,给我们娱乐!
最初的热闹场面来自烟。一个病人要烟,郭海平果真递给了他一根,病人感到惊奇:抽烟也能满足啊!接下来几天又来了六七个无心画画的病人,护士告诉郭海平,他们其实是来索要香烟的,因为医院规定每人每天只发10支烟,而郭海平这里则是有求必应,几乎无限量供给。这里香烟显然比艺术更受欢迎。
在画室负责维持秩序的医护人员们不懂艺术,然而当他们看到病人们在画纸前开始涂涂画画时,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奇——在和病人打了五六年甚至十几年交道之后,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病人们的另一种精神状态,涣散的目光聚成一点,有时甚至目光炯炯。
画画时,女病人通常比男病人热闹,一边画一边议论。当男女混合在一间大厅内,他们彼此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偶尔有男士去女方画桌看一眼,姿态举止也会很绅士,轻轻来轻轻去。比较而言,倒是女士们自始至终没兴趣去看一眼男士的作品。
绘画的材料,最受欢迎的是铅笔和油画棒。色彩鲜艳,使用畅快。“可能像水彩、油画颜料等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来掌握,所以病人很少用这些。”
郭海平还发现,精神病人只要拿起笔,就直接开始画,没有迟疑没有思考,“而正常人,如果让你画个东西,你要想一会,或是觉得别人在看,还会不好意思,而精神病人从来不会。”
白天繁忙,晚上寂静。
画室旁的一间空屋子,就是郭海平的卧室。其实就是偌大的屋子里摆张床。刚来时,夜晚,四层楼就住他一人。窗外山风呼啸,吹动窗子,会在空荡荡的室内发出回音。郭海平很恐惧,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壮胆。慢慢地,他觉得不再害怕了。他与精神病人已相处两个月了。
“大师们”
“大师们”
王军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用橡皮、笔、茶杯当直尺和圆规用。他的多数绘画都是一些直线、曲线和圆构成的机械组合。第一幅画是工厂车间里吊在顶棚的自行车,每画完一幅,他就会详细地给看的人讲解。他还是唯一能适应马克笔的人,每当画完,会一一套上笔套。“很喜欢画画”。只有看到自己的画是规规矩矩,他才能感到安心和踏实。
王军原本是个农民,身材厚实,满脸敦厚。他清楚自己住进医院是因为中断了吃药。“但吃了药就没力气种田了”,他这样告诉郭海平。
他有两个儿子要上学,村里人住进小楼,他还住在破烂的平房里,加上儿子要结婚,没房子就没法结。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崩溃了。他的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发病时,多次殴打自己的家人,冲砸别人家,还要用刀杀人,终于被村委会和民警送到祖堂山。
郭海平觉得,王军之所以爱画机械,是希望自己像机械一样有强大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而用色的多彩均衡,像中国的年画,潜意识里表达中国农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小女孩李丽作画时不愿有任何人打扰,旁边如果有人,她就用手臂把图纸圈起来,扭过来憨憨地看着那人。而张玉宝则是习惯性地晃腿,什么话也不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目光漫散地看着画纸的上方,为了进入创作状态,他把桌子摆到了一个角落里。
46岁的余丹自称“格格”,时常描述她作品当中的故事,主角总是“大肥种”和“小肥种”,她描绘报幕员致完辞,“大肥种”唱歌,“小肥种”跳舞,至于“肥种”是什么她也不解释。她还会唱越剧,张口就能编一段什么“琴弦已断,你休提它!”思路敏捷令人惊讶。
除了画画,病人还会写诗。有首诗写道:
高高在上一美人
十四、五、八正当春
十七八得了病
一过三十就归荫
郭海平“考证”后发现,这是群体所作的诗。
一起入精神病院的,还有拍纪录片的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蔡寅羽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来拍片之前担心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精神病人会冲上来猛咬他一口,到里面之后,他发现完全没有这种想像中的危险,相反,他发现这些病人十分可爱,而且表现欲特别强,时常在他的镜头前手舞足蹈一番。
在这个画室里头没有理性思维、明晰的逻辑,一切都如生命自身那样本真,自然。
而让郭海平感到过瘾的是,他拿了一大堆中外名家的画让病人们欣赏解读,发现这些人说话“幽默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解释没有顾忌的,不像平常人的解释怕脱离主题,怕欣赏水平不高,怕说得不准确,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一次张玉宝打开了郭海平自己的画册,瞄了两眼之后低声说:“柔中带刚”,如此精炼的评语让郭海平吃惊不小。
禁锢
然而,这里毕竟是精神病院,禁锢对“大师们”来说无所不在。
15岁的唐小波,被诊断是“精神障碍迟滞”。每回作画不过十分钟就得放下手中的彩笔,“手抖”、“想睡觉”,原因是“药吃的”。在这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病人一作画就满头大汗浑身湿透,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抗精神病药物,画画时他们明显体力不支。
对于服用药物,郭海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你去查精神病的书籍,第一句话都是病因不明,到现在为止药物只是控制他的症状,有很多副作用。在不知病因的情况下,就用这种手段来干预,这是违反自然伦理的事。”
在反复讨价还价后,医生勉强同意让少数几个症状较轻的病人减药,因为医生担心大多数病人减药之后会进入难以自控的亢奋状态。
张玉宝此前脑子里总是浮现幻觉般的影像,后来就没有了。他每天减去两颗药,天天画画放松心情。他开始有意识地画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回忆,公共汽车站、澡堂、厨房、市民广场。
作画成了病人们最快乐的时光。抽烟,抖脚,削铅笔,调颜料,看书,勾线条,上色,题字,释放怪诞的念想,讲笑话,唱歌,和“郭老师”谈艺术观,这更像是一场穿着蓝白条色精神病服的自由“艺术家”的聚会。
当一大批作品出现在院长王明忠和病区主任王玉面前时,他们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些病人来到医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在从事艺术创作时那么生机勃发、才思泉涌。院长当场决定,同意郭海平在祖堂山多呆两个月。
郭海平大喜过望。
“疯人”郭海平
“疯人”郭海平
郭海平对“精神病和艺术”的关注并非突发奇想,在很多人眼里他本人就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怪人。这次活动的另一位发起者聂鹰是精神病医生,他甚至开玩笑地说,郭海平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22岁之前的郭海平一切跟常人无异,22岁接触艺术之后突然就“疯”了,他觉得自己在生活中老是受挫,事业、家庭、甚至上大街走路,到处充满了障碍和限制,生不如死。于是,他白天睡觉不上班,晚上起来涂涂画画。郭父认为是艺术把儿子害成这样的,把他全部的画都烧掉了。
1983年冬天,郭海平和一个朋友策划了更为惊人的举动——这回他们要偷渡越境。他从家里偷了几个银元放到鞋底下,揣着几张粮票,和朋友背着书,扛着一个油画箱就坐火车到了广州。由于语言不通,无处投宿,冬天只好睡在野外,没钱吃饭的时候就给人画肖像。终于有一天,他们走到了澳门边境,突然树林里出来两个持枪武警:“你们已经到了禁区,我们随时可以开枪击毙你们!”
那时候还有“叛国投敌罪”一说,直到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郭海平和他的朋友的时候,两个疯狂的文艺青年才猛醒过来。
年轻时离经叛道的经历给了他边缘感,也形成了对边缘群体的关注。
这次偷渡不遂之后,郭海平回到南京,彻底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
争议
然而,对郭海平入驻精神病院的动机,外界猜测不断。
早在去年底,南京的一家媒体就“是作秀还是艺术”提出了质疑,而在最近,更有媒体怀疑这是一场骗局,有人认为郭海平是拿着病人的作品来卖钱。更大的争议是针对精神病人作品本身。有人直言:将精神病人的涂鸦称为“凡·高式的作品”是哗众取宠言过其实。凡·高虽然也是精神病患者,但他毕竟系统学习过光线、配色和构图技巧,远非普通精神病人可比。一位南京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不客气地批评:郭海平是半路出家搞艺术,对艺术的理解十分浅显。
批评意见也来自普通观众。展会现场,两个中年人在看了精神病人的雕塑作品后,表达了极大的困惑。“这样瞎捏一团的泥巴也叫艺术吗?随便一个普通人都能捏出这种东西!”一位网友在网络上看了作品之后发帖说:“我儿子也会画这样的图。怎么没有人说他是艺术家?”话中嘲讽之意显见。对此,郭海平回应说:精神病人的作品技法上可能确实有幼稚的地方,但内容上是心智成熟的产物,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和非常独特的视角,这三点足以构成其作品的独特艺术性。
目前,国内对艺术与精神病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展起来,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观察。实际上,国外对“疯狂”与“天才”之间关系的关注最初也源于经验的神秘感,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巴尔扎克、凡·高、蒙克、叶赛宁、庞德等人身上的天才被认为与某种精神上的疾病有充分的联系。但是,如何解释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它们的价值有多大?这成为医学界和艺术界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而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似乎都还遥遥无期。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心理、艺术治疗教师孟沛欣博士长期对绘画艺术治疗有系统研究,她曾经在北京安定医院进行过为期一年的绘画艺术治疗研究,试图通过绘画艺术治疗形式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她认为,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状态确实有利于释放潜意识,这对艺术创作肯定是大大有利的。
自然、率真正是郭海平等艺术家反复提倡的艺术价值。但是艺术是否仅仅是求真,或者说只有求真是否足够?这些问题如同繁多的艺术流派一样,每个人有不同见解。
像更被普通人接受的精神病人张玉宝的作品,反映出这位精神病人拥有出色的将抽象和具象自由转化的能力,而更多精神病人的作品还只是对个人感受的纯抽象表达。这是否正是“非理性”的他们与“理性”的社会大众沟通的一大障碍? 郭海平的试验无力证明这些问题。
文学批评家王干在参观完作品后表达了遗憾:“艺术是直指人类心灵的,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真正有震撼力的作品。”更多人认为这次艺术尝试的价值更在于活动的本身而非作品。
无畏的幸福的微笑
无畏的幸福的微笑
此次作品来北京展览,祖堂山的“大师”们并不知道,医院也十分小心,出版的书决不让病人看到,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所有作品都采用化名,涉及病人的图片脸部都打上了马赛克。这种出于保护病人的初衷往往会令病人感到愤怒:凭什么我的作品不能署自己的真名?凭什么我的脸被涂花?
郭海平说,他的希望是以后能让病人以真名真姓像艺术家那样堂堂正正地出画册,让这个最边缘的群体光彩地出现在中国的艺术界里。
在精神病院的三个月里,郭海平与一位名叫小五子的病人交情很深。要离开祖堂山的时候,他跟病区主任王玉说,能不能请小五子做病人代表在欢送会上说几句话。王主任告诉他,小五子最近拒绝吃饭,医院就采用鼻食的方法给他灌,可是他不服从,“哗啦”一下把管子整个从肚子里抽出来甩在地上。
这么有艺术天赋的一个人,一下子到这个状态,郭海平听到,伤感得一塌糊涂。那天的日记,他写道:我无法回忆任何一位病人在画室里经历的一切,因为任何回忆都会让我感到无比的悲哀和绝望。
后来小五子灌过鼻食以后,王玉又带他来画室,他一直沉默地望着窗外的天空。12月的南京,寒意深凉,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在风里弯着。
郭海平结束了癫狂艺术的试验。 “我和医生看病人的视角不同,医生是俯视他们的,我一开始是平视,最后我就仰视他们了。他们都在天上啊,他们太牛逼了!像天使一样俯视人间!”
“精神病人经常笑得幸福得不得了,医学上他们叫傻笑,我说呆B,医生根本不懂,这是一种无畏的幸福的微笑。”
虽然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疯狂”与“艺术”之间到底有什么玄机,但是很多像郭海平这样的艺术家相信:虽然很多对正常人开放的门对精神病人关闭了,但上帝有一扇门总是对他们开着,那就是艺术之门。 (文中出现的精神病患者均采用化名)
但即使不少人对此次艺术创作本身价值持有异议,绝大多数人还是对郭海平的这次试验表达了钦佩。“郭海平的这次活动是开创性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么成功地向普通公众展示了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孟沛欣评价说。
患有精神病的艺术大师
患有精神病的艺术大师
凡·高
1853年生于荷兰,被视为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艺术大师。面对当时冷酷和污浊的社会现实,这位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错乱,病发之时陷于狂乱,病过之后则更加痛苦。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不停地作画。在精神接近崩溃的时候,他曾经用剃须刀片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在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七幅向日葵后,1890年他由于精神病而自杀身亡。
爱德华·蒙克
蒙克(1863-1944)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挪威艺术家,西方表现主义绘画艺术的先驱。5岁那年母亲患肺结核去世之后,父亲抑郁的神经开始强烈地感染蒙克。13岁时,他年长两岁的姐姐也因肺病去世,再次刺激了蒙克的神经,接下来,妹妹也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蒙克在1908年精神分裂了。但在接受治疗后,他仍以很高的热情坚持创作。他的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
草间弥生
1929年生于日本长野,为日本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具有多重创作身份:画家、雕塑家、即兴表演者、小说家,同时也是服装设计师。她从小就患有精神病,并一直生活在幻觉的折磨中。她的少年时期过得很艰难,时常有自杀企图。至今常年自愿居住在精神疗养院,并以70多岁的高龄继续从事艺术创作。
他们是谁?精神病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
在医学上,“精神病”有很多类,包括: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性精神病、更年期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病等。主要表现在由于丘脑、大脑功能紊乱而引发的感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方面表现异常。精神病患者可能表现出严重的心理障碍,其认识、情感、意志、行为均可能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
然而,医学上对“精神病”的定义和患者的强制治疗,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以哲学、历史和艺术为代表的人文学者的强烈反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来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于1961年完成的作品《疯癫与文明》。福柯通过详细考察西方精神病院制度形成的历史,在书中提出:“疯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中形成的文明现象,精神病并非一种确切意义上的“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在西方中世纪以前,疯癫一直被认为是和“理性”一起构成文明深度的两个元素,到了16、17世纪人们开始将疯癫与愚蠢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8世纪末,疯癫才被命名为一种精神疾病,“精神病人”被实行禁闭政策。在福柯看来,“疯癫”纯粹是理性人群对非理性人群加以迫害的历史。
而在艺术界,实际上很多艺术家也并不同意“精神病人”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相对于经验的意志,生命本身的意志更应该被强调,而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肯定人的非理性的价值。诸多艺术家以此为由反对以“精神病人”给这些非理性人群命名。在艺术史上,很多大师就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其中凡·高、蒙克这样的天才人物。
也并不是所有精神病医学家都选择与哲学家艺术家对立。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医学家塞拉·隆布罗索曾经专门写了一部专著《天才的人》,来详细论证“极端聪明的人都是极端癫狂的”,他坚信“事实是,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的人。还有多少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
医学上对“精神病”的定义和治疗手法广受争议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精神病都是“病因不明”的,目前用于治疗的药物成分大部分是神经阻断剂,只是克服了精神病的表现症状,对患者神经系统却有很大伤害。
中国政府卫生部门于2005年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的重型精神病病人总数达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达600万人次,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0万名的速度增加。如何建立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机制,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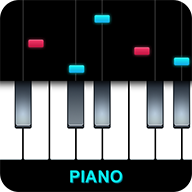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