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与艺术相距究竟有多远?带着这个疑问,南京当代艺术家郭海平住进了市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探索。他带来了画板、蜡笔、油彩、橡皮,还有茶和香烟,他让长期与世隔绝的精神病人们在放松的环境中,拿起笔,任意涂抹他们心中所想的任何画面。他说这是一场试
“大师们”
“大师们”
王军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用橡皮、笔、茶杯当直尺和圆规用。他的多数绘画都是一些直线、曲线和圆构成的机械组合。第一幅画是工厂车间里吊在顶棚的自行车,每画完一幅,他就会详细地给看的人讲解。他还是唯一能适应马克笔的人,每当画完,会一一套上笔套。“很喜欢画画”。只有看到自己的画是规规矩矩,他才能感到安心和踏实。
王军原本是个农民,身材厚实,满脸敦厚。他清楚自己住进医院是因为中断了吃药。“但吃了药就没力气种田了”,他这样告诉郭海平。
他有两个儿子要上学,村里人住进小楼,他还住在破烂的平房里,加上儿子要结婚,没房子就没法结。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崩溃了。他的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发病时,多次殴打自己的家人,冲砸别人家,还要用刀杀人,终于被村委会和民警送到祖堂山。
郭海平觉得,王军之所以爱画机械,是希望自己像机械一样有强大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而用色的多彩均衡,像中国的年画,潜意识里表达中国农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小女孩李丽作画时不愿有任何人打扰,旁边如果有人,她就用手臂把图纸圈起来,扭过来憨憨地看着那人。而张玉宝则是习惯性地晃腿,什么话也不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目光漫散地看着画纸的上方,为了进入创作状态,他把桌子摆到了一个角落里。
46岁的余丹自称“格格”,时常描述她作品当中的故事,主角总是“大肥种”和“小肥种”,她描绘报幕员致完辞,“大肥种”唱歌,“小肥种”跳舞,至于“肥种”是什么她也不解释。她还会唱越剧,张口就能编一段什么“琴弦已断,你休提它!”思路敏捷令人惊讶。
除了画画,病人还会写诗。有首诗写道:
高高在上一美人
十四、五、八正当春
十七八得了病
一过三十就归荫
郭海平“考证”后发现,这是群体所作的诗。
一起入精神病院的,还有拍纪录片的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蔡寅羽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来拍片之前担心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精神病人会冲上来猛咬他一口,到里面之后,他发现完全没有这种想像中的危险,相反,他发现这些病人十分可爱,而且表现欲特别强,时常在他的镜头前手舞足蹈一番。
在这个画室里头没有理性思维、明晰的逻辑,一切都如生命自身那样本真,自然。
而让郭海平感到过瘾的是,他拿了一大堆中外名家的画让病人们欣赏解读,发现这些人说话“幽默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解释没有顾忌的,不像平常人的解释怕脱离主题,怕欣赏水平不高,怕说得不准确,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一次张玉宝打开了郭海平自己的画册,瞄了两眼之后低声说:“柔中带刚”,如此精炼的评语让郭海平吃惊不小。
禁锢
然而,这里毕竟是精神病院,禁锢对“大师们”来说无所不在。
15岁的唐小波,被诊断是“精神障碍迟滞”。每回作画不过十分钟就得放下手中的彩笔,“手抖”、“想睡觉”,原因是“药吃的”。在这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病人一作画就满头大汗浑身湿透,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抗精神病药物,画画时他们明显体力不支。
对于服用药物,郭海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你去查精神病的书籍,第一句话都是病因不明,到现在为止药物只是控制他的症状,有很多副作用。在不知病因的情况下,就用这种手段来干预,这是违反自然伦理的事。”
在反复讨价还价后,医生勉强同意让少数几个症状较轻的病人减药,因为医生担心大多数病人减药之后会进入难以自控的亢奋状态。
张玉宝此前脑子里总是浮现幻觉般的影像,后来就没有了。他每天减去两颗药,天天画画放松心情。他开始有意识地画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回忆,公共汽车站、澡堂、厨房、市民广场。
作画成了病人们最快乐的时光。抽烟,抖脚,削铅笔,调颜料,看书,勾线条,上色,题字,释放怪诞的念想,讲笑话,唱歌,和“郭老师”谈艺术观,这更像是一场穿着蓝白条色精神病服的自由“艺术家”的聚会。
当一大批作品出现在院长王明忠和病区主任王玉面前时,他们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些病人来到医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在从事艺术创作时那么生机勃发、才思泉涌。院长当场决定,同意郭海平在祖堂山多呆两个月。
郭海平大喜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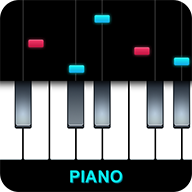






网友评论